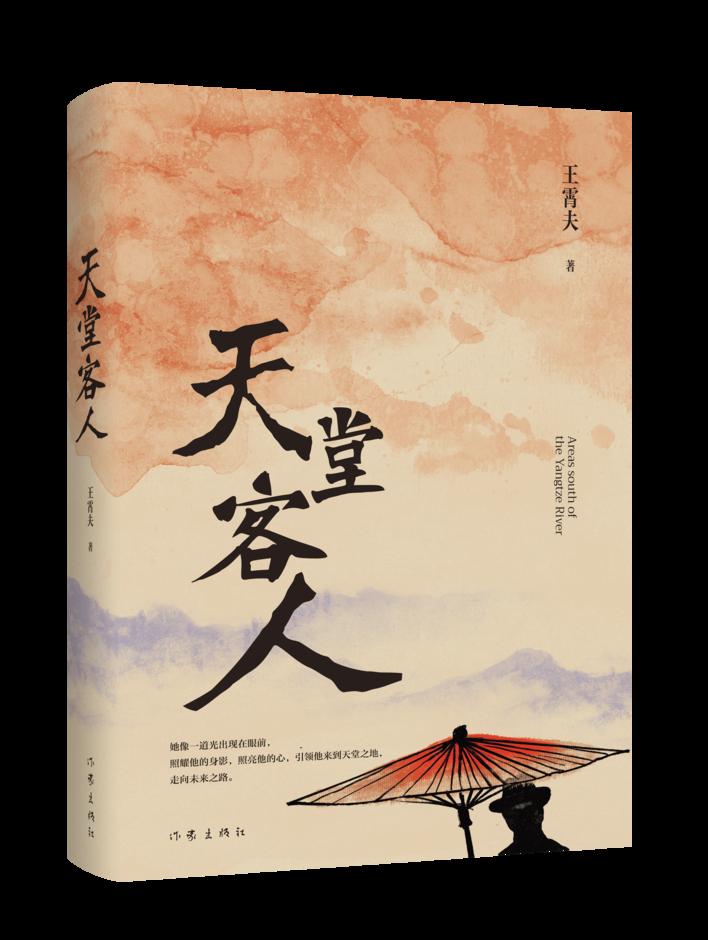那时候,已经是南京中华民国政府的时候,在习惯帝都皇城说天下、坐北朝南看东西的大多数北平人眼里,江南之城杭州,也许是一个有小山色、过小日子、做小生意、写小诗文的遥远之地。但在极少数也许是极个别北平人眼里,例如在伏申眼里,杭州之所以是向往之地,是因为杭州的女子。
十分偶然,也是天意如此,伏申在蒙昧初开、少年烦恼之时,生平见到的第一个杭州人是一个女子,当时他是一个不起眼的旁观者,没有与她交流的机会,但仿佛有一道柔和的光芒,照亮了他;第二次见到的,还是这个杭州女子,他举着旗帜,看到她在鲜血、飞雪和黑暗中,如雕像那样站立,像烈士那样歌唱,从此情有颤动,心有肃然;第三次见到,仍然是这个杭州女子,在非常特别的环境下,在不多言说的秘密中,他与她在北平监狱里,相拥取暖,共度寒夜。
一次又一次,他见到的,都是同一个杭州女子。
每次见到,她都邀请伏申到杭州做客,届时她一定尽地主之谊,盛情接待,倾其所好,一定让他宾至如归,感受美好,乐而忘返。然而,当他迢迢千里,奔波辗转,终于来到杭州,更多见到的是别的杭州女子,却没有见到这位向他发出邀请的杭州女子。于是,他就一直等待,等待她陪伴他,一起进入她讲述过的、描绘过的杭州。等待的岁月里,没有她的杭州是陌生的、空洞的、不宜人居的,是容易被人捉弄的。
甚至,让他成为克里森医生的催眠病人和释梦对象。
在外国人,也就是精神科医生克里森眼里,看到的是杭州的病人。杭州很少有人想到,或者不愿意想到,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之日,就是进入中华民国末期之时。光复以来,短短数年的混乱无序和毫无逻辑,足以暴露一个庞大政权断崖式崩溃的败象,足以使杭州这样的偏安之隅不再令人感到惬意。正是光复以来短短数年的变故刺激和时运无常,使克里森的病人越来越多,直到他离开杭州前,仍然十分尽心地为他们治疗,不管他政治立场如何,不管他属于什么阵营。他是从上海离境回欧洲的,但在他心里,最后只向杭州告别。告别是为了把灵魂,至少一部分灵魂留下,在中国,杭州是最适合用来告别的地方,因为杭州是人间天堂,心留天堂,何其幸运。之后数年里,对从马可·波罗书中听说过杭州的家乡人民,他不吝词语,津津乐道,极尽赞美,广为宣传。后来,他曾试图从西柏林越境到民主德国的东柏林,然后前往社会主义新中国,而且目的地是杭州,因为那里还有他的病人。但他最终放弃了。
后来,他希望他的著作《最忆是杭州》能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让他的病人看到,他是多么怀念他们。为此,他写信向伏申求助,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复。他在信中说,解放以来,人民的杭州一定更美好了,因此他深信,伏申仍然人在杭州,仍然没有回到北平,尽管北平已经再次成为首都北京,他深信,解放以来,伏申个人的命运,家族的命运也一定会更如意。
克里森对“解放以来”充满想象和期望。在未来的《最忆是杭州》中文版序言中,他这样解释,新中国人民对“解放”有最美好最切身的体会和感受,无论公开场合和私下谈论,一提到现实状况,一提到时间概念,都会用“解放以来”或者“1949年解放以来”一词,表示对一个特定时代、特定阶段的特殊情感,就如国民政府后期,也就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日至国共内战胜败即将定局这一时期,当时的人们总是说“光复以来”或者“1945年光复以来”。然而,天下大势,不可逆转,“光复以来”很快被“解放以来”取代了,而且取代得那么彻底。当然,随着社会进步、世事变迁,总有新生的、最适合时代和人民心理的,更科学也更通俗的新概念和新状语面世。
克里森与伏申最多最深的交集,是在1945年以来的那些日子,也就是故事发生的那些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