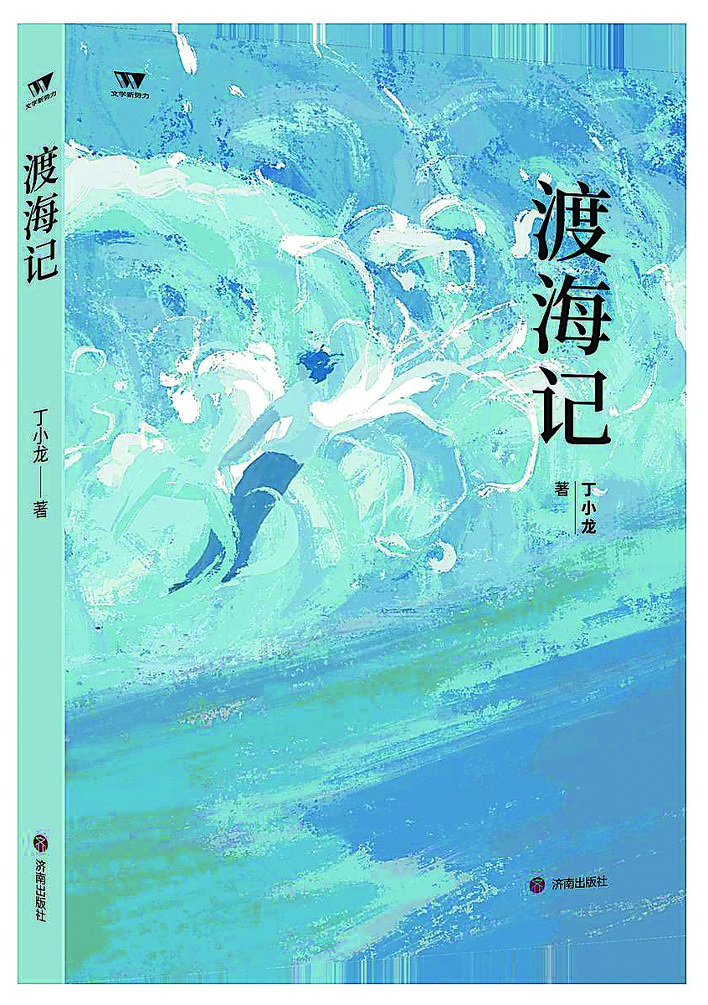□庞 洁
《渡海记》是丁小龙最新的中短篇小说集。无论是讲述老年的孤独(《天涯倦客》),还是婚姻中那“透明的炼狱”(《渡海记》),再或家族命运的轮回与羁绊(《净土》)、艺术家的精神困境(《万象》)等诸多现实题材,丁小龙以深沉而节制的笔触、娴熟的技艺和小说家独有的睿智、悲悯审视人间百态,讲述人的困顿与挣扎,展现生存之危机与命运之荒诞。尤其触动我的是小说中对“死亡”的思考与书写,体现了丁小龙富于哲思的写作意识。作为年轻的小说家,这种果敢比才华更为难得。小说的艺术价值在于其象征主义手法、娴熟的对话和人物的成功塑造。
《渡海记》是如此静谧而独自地面对残酷的时间荒原,面对人生海海的辽阔与绝望。“独自”却不是喃喃独语,他感受着海面的风云变幻,有时候像在海边独自徘徊的梦游者,即便在最困顿的暗夜,也提醒自己“到灯塔去”。没有这样的写作信仰或人生信念,我们如何在苍茫的人世救赎自己?丁小龙借主人公说道:“人这一辈子,就是渡海,没有谁能逃过劫难,躲过灾难。”因此,他笔下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灵魂,也在苦苦找寻尘世间的灯塔,即便发出的只是微光,却总能让人有勇气面对苍穹。
作为多年的好友与文学同道,我和小龙有很多次愉快而深入的探讨,分享各自喜欢的作品、电影、音乐、艺术等等,当然偶尔也聊及当下的生活。但我这是第一次相对系统地阅读他的作品,小龙的阅读量惊人,但他绝不是一个孜孜不倦谈论“我”的人,作为一个真诚的听众,他更多的是谦和地聆听。在他的小说中,我看到了他的另一面,某些小说中的情境让我联想到我们曾经的对话,彼时他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及,而将浓墨重彩的情感以及某些不可言说的部分放在了作品中,这使得他的小说呈现出稳定的内核,而不是为了在流量时代争得一席之地而采取的必要或非必要的“妥协”。写作本身首先作为个体经验的表达,也在主动筛选自己的读者,很多作家太怕落选、落伍。难能可贵的是,丁小龙的小说既在克服“轻”,也在克服“重”。可以说,丁小龙已经构建了其独有的小说秩序。他的小说还拥有难得的古典音乐的气质,具有非常严谨的音律结构,这大抵和他受了些古典音乐的熏染不无关系。比如《浮士德奏鸣曲》,写一位研究《浮士德》的学者的精神泅渡,他直接以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开篇。同古典交响曲的结构一样,这篇小说由四个乐章构成,层层推进而浑然一体。
我愿称丁小龙为那一类有“教养”的作家,将其全部的深邃都藏在语言里,露出的部分同样静默如海。他的小说没有炫技的表演,他敬畏语言与经验,能看出他对小说艺术的精心乃至孜孜矻矻的研磨,从他的作品命名上就能看出他所做的努力。小龙在近年写小说之余还创作了很多散文和诗歌,虽然这也是他极少主动提及的。在某本杂志上,我读到了他的诗歌,那些或隐秘或空灵的诗句可以视为他的思想笔记。与他的小说对照,就几乎能肯定是出自同一作者。我曾当面直言“你写得比我想象中的更好”,他谦虚地笑,我当时引用了弗罗斯特的诗。我说,即便我们(我提到了为数不多的几位可以互称知己的朋友),走的就是“人迹罕至”的那条路,但那又何妨呢?他点头。
我喜欢昆德拉的一句话,他说小说是这样一个东西,所有人都能从中获得理解,不管你是好的、坏的、平庸的还是什么样的。人的处境、选择、尊严或者其他各种东西能够变成你要表达的重要东西之一。小说当然不是对号入座的生活,作为一种语言“装置”,有些艺术家拼命地将自己放进去,有些则是努力摘出来,艺术家选择完全冷眼旁观,抑或把自己作为舞台的一部分,就取决于自己的艺术理念,及多大程度上“看见”自己。
我记得小龙有一次聊黑塞的《悉达多》,他说这是关于觉醒者的故事,“是关于一个人如何在道路上发现自我、怀疑自我、否定自我与再造自我的心灵之书”。我没有问过他,但以我的了解,他想写的应该也是这样的心灵之书。菩提树下,沙门乔达摩把甚深的定力集中在深入观察自己,再把他的洞察力照射到所有产生痛苦的精神状态上——恐惧、愤怒、憎恨、傲慢、嫉妒、贪欲和无明。他体悟到解脱之窍门是要破除无明,深入实相中去直接体验亲证。而作为小说家的丁小龙,他想做的以及一直在努力实现的,同样是破除无明,成为通向彼岸的摆渡者。
(作者系作家、文学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