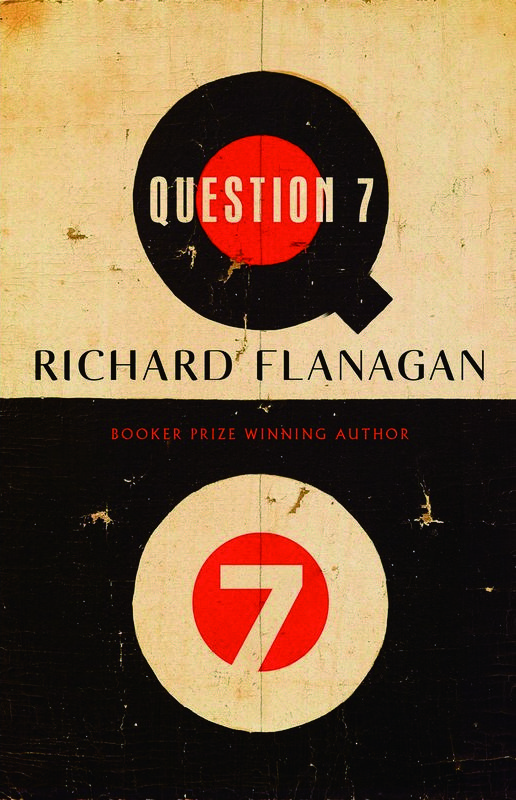2023年年底,澳大利亚作家理查德·弗兰纳根出版新书《第七个问题》。这是作者出版《深入北方的小路》(获2014年布克文学奖)之后,创作的一部极佳作品。这本小说里有文学巨匠H.G.威尔斯和丽贝卡·韦斯特之间的爱情纠缠,涉及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关系错综复杂的核物理研究的世界,还有弗兰纳根被困在危险的塔斯马尼亚河急流中的真实经历回溯,以及他父亲的二战经历。这本书像是历史小说,也是自传、随笔和哲学思考,它体现了作者作为小说家善于讲故事的本领,也展现了作者对于世界未来和人类生存状态的思考。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这本书是为了表达对过世父母的爱与思念。
《第七个问题》到底是什么?
小说的名字来自于契诃夫的一篇短篇小说《癫狂数学家的问题》。该小说创作于契诃夫的青年时代,小说中一共有八个问题,其中第七个问题如下:“1881年6月17日星期三,一列火车必须在早上3点离开A站,才可以在晚上11点到达B站;然而,就在火车即将出发时,接到命令要求火车必须在晚上7点前到达B站。男人和女人谁更长情?” 这不是一个脑筋急转弯的问题。如果我们按照正常的逻辑思维看,这是一个无厘头的问题。如果是关于火车的问题,根据已知条件,火车根本无法按时到达B站,所以这个命令是一个无法执行的荒唐命令;那么如果是关于男女谁更长情的问题,是不是也同样疯癫且无解?
关于癫狂或者疯狂,在无数的文学作品中,被浪漫化的癫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堂吉诃德,再比如麦克白。在福柯看来,疯癫作为一种精神疾病,随着医学的进步,也许它会像麻风病和肺结核一样最终可以医治。但是疯癫的异化性一直具有神秘的吸引力,“众人皆醉我独醒”,癫狂者可能掌握着普通人无法感知的真理。所以,疯癫的历史实际是理性的历史被隐藏的另一面。不论是契诃夫,还是福柯,他们都看到,癫狂的关键问题或者隐喻并不在于癫狂本身,而在于它凸显了人们最不愿去正视和承认的有关人存在的真相。《第七个问题》实际上是关于一系列问题的思考,时刻提醒我们注意那些被压抑在黑暗之处的弗洛伊德式的无意识。
一部影响历史走向的小说
读者一般都熟悉这样的历史: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开始,美国核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起草了一封致罗斯福总统的信,敦促他资助一个开发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项目。西拉德知道要想增加他建议被采纳的机会,应该说服爱因斯坦在这封信上共同签名。而爱因斯坦的赫赫名声确实发挥了作用,罗斯福同意实施曼哈顿计划,然后就有了广岛、长崎和冷战这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发生。但是,是什么启发西拉德想到原子弹计划?答案是西拉德读了H.G.威尔斯的小说《获得自由的世界》。西拉德曾这样回忆他所受到的启发,“1932年,当时我还在柏林,读了威尔斯的一本书,书名是《获得自由的世界》。这本书写于1913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一年。书中描写了发现人工放射能的情形,并把这一发现的时间放在1933年——后来事实上也确实是在这一年发现的原子能。接着,他描写了大量释放原子能用于工业用途、原子弹的方面,以及另一场世界大战”。就是因为从这本科幻小说中获得的灵感,西拉德找到了使链式反应持续进行的方法,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托他转交给美国总统罗斯福,警告总统“一种威力极大的新型炸弹”有可能被制造出来。为了制衡德国,美国的“曼哈顿计划”诞生,然后才有广岛与长崎的原子弹投放。我们都知道罗斯福或者美国等诸多因素在历史中的重要性,但是弗兰纳根这部小说溯源到了一部小说所发生的作用。
在《第七个问题》中,弗兰纳根结合自身作为小说家的丰富的想象力和作为历史专业毕业生的史料查找能力,给大家讲述了一个由错综复杂的爱恋故事所引发的历史走向的改变。这个爱恋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英国科幻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G.Wells,1866-1946)和英国作家兼女权主义者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1892-1983)。中国读者多熟悉H.G.威尔斯的《时间机器》和《隐身人》等小说;相对而言,丽贝卡·韦斯特并不是那么被中国读者所熟知。她是一位在英国非常活跃的妇女参政权论者和社会改革家,不仅为英美很多报纸和杂志撰稿,也写了大量经典小说。关于他们爱情的描述,特别是女方的心理,丽贝卡·韦斯特的小说《世纪传奇三部曲》和《太阳花》等都可以说是一种真实写照。一个爱恋着有妇之夫的女子,尽管外表上是一个强势的公众女性,她在心中还是渴望结婚生子,拥有自己的家庭和安全感。对于这位女作家,连萧伯纳都赞叹,“她的文字智慧而犀利,这是我所不能及的”。丽贝卡·韦斯特的观点应该也影响着H.G.威尔斯,比如她在《黑羊与灰隼》中曾说过的:“如果在接下来的几百万代人中,每一代人中只有一个人不断地探究自己命运的本质,即使命运剥夺了他的生命并殴打他,总有一天我们将解开宇宙之谜。”
1913年,感觉到自己已经被丽贝卡·韦斯特吸引之后,为了抗拒,也是恐惧自己被这种爱所控制,H.G.威尔斯收拾行李去了瑞士,并在那里创作了小说《获得自由的世界》。他将自己的恐惧转移到对世界毁灭的恐惧。这部小说题献给索迪(Frederick Soddy,1877-1956),1921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英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索迪于1910年提出了同位素假说,1913年发现了放射性元素的位移规律。他为放射化学、核物理学这两门新学科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H.G.威尔斯阅读了索迪所写的一本关于镭元素介绍的书籍。他敏锐地看到了这种元素的应用可能产生的潜在威力,所以才创作了这部小说。严格地说,这部小说的意义并不是预测原子弹的制造技术,而是预言了核战争的可怕后果。在乔治·奥威尔看来,直到1914年,威尔斯都是“一位真正的先知”,“出生于本世纪初的有思想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是威尔斯所缔造的”,这其中也包括从威尔斯小说中找到灵感,而想到给总统写信的利奥·西拉德。
对战争残暴的反思
对于二战期间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这个历史事件,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反思。每年的8月6号和8月9号,日本政府会努力将世界的目光聚在广岛、长崎两个地方。让人们听到幸存者、生还者对于死去家人的缅怀。日本政府的领导人会充满深情地去相关的纪念碑处吊唁,哀悼在原子弹爆炸时伤亡的民众。但是,如果根据弗兰纳根父亲的真实经历,在广岛、长崎被轰炸的时候,他就被关在一个战俘营中。这个战俘营是当时日本军队设置的无数战俘营之一,他要参与修建一条死亡铁路,每一根铁轨下都有无数战俘和平民的亡魂。这些死去的,或濒临死亡的战俘,他们所经历的苦难,与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给日本人所带来的痛苦相比,谁更加痛苦?这个问题与契诃夫的那“第七个问题”性质相同。
对于弗兰纳根而言,他自己家人的真实经历例证一个观点,二战中使用原子弹确实加速了战争结束,避免更大规模的伤亡和破坏。二战后期,日本政府表现出极强的抵抗意志,拒绝接受盟国的无条件投降要求。传统的战略轰炸未能迫使日本就范,在战俘营中的弗兰纳根的父亲已经到了自己承受的极限,以为生命即将完结,永远无望回到自己的故乡——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恰恰是原子弹的巨大威力给日本政府和民众以深刻的警示,迫使他们接受了现实,承认战败,所以战俘才得以被释放。否则弗兰纳根的父亲、战俘营中的军医邓禄普上校,以及成千上万的盟军士兵就不可能返回祖国。关于战俘的凄惨经历和死亡的惨状,弗兰纳根2014年获得布克奖的小说《深入北方的小路》有丰富的描写。但是有一点需要明确,弗兰纳根的小说不是鼓励仇恨日本士兵。他的创作主旨是反思战争的起源,从中吸取教训,并理解——对于战争苦难历史,我们不能忘记,但是我们不能让自己的内心充满仇恨,因为仇恨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吞噬人类。
在《第七个问题》结尾处,作者的一段话非常有寓意,他说:“我们要先有梦想,才有方向。有时我们发现自己生活在别人的梦境和噩梦中,于是我们重新做梦。你现在正在读的这本书,只不过是我写给我父母和我的故乡岛屿的情书。那是一个已经消失的世界,就是因为一个多世纪前,另一位作家写了一本书,几十年后,那本书如此强大的力量抓住了另一个人的思想,以至于被重塑为世界的现实。那是一个恐怖的故事,源于他对爱的恐惧,完整的、没有尺度或界限之爱,于是他就创造了一种无限制的毁灭观念来取而代之。这样,世界就生成了一本书,而这书又生成了一个世界。”对于作家弗兰纳根而言,对父母和家乡的爱让他不断地写作,同时他推崇文字和小说核链式反应的力量。因此,在这部小说中,他结合历史,家族史与想象,深描作家H.G.威尔斯的个人经历如何影响了一部小说的创作,而这部小说又如何影响了二战的走向和弗兰纳根一家人的命运。这再次印证了一句话,历史中存在着无数的偶然,但无论偶然的细节如何,保持善意与爱都是至关重要的。
(作者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