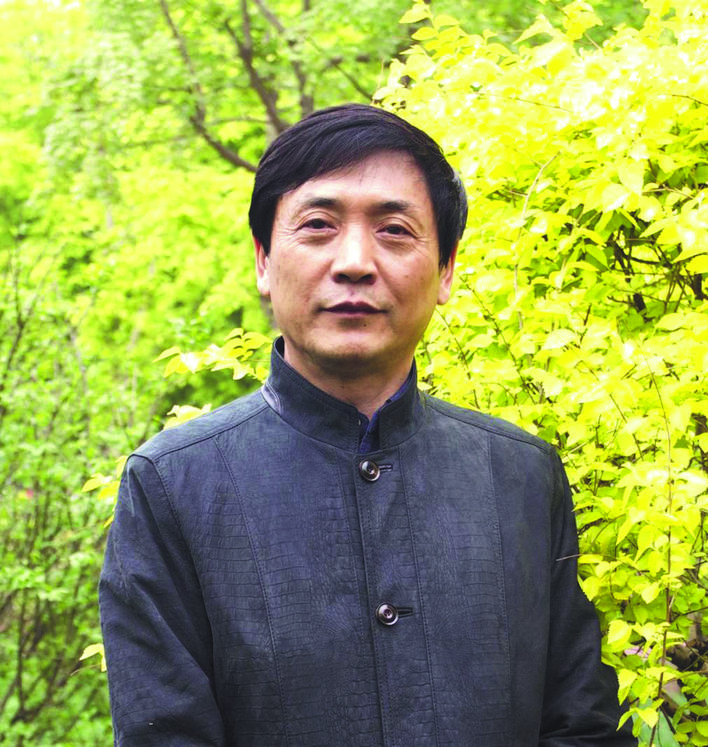中国是儿歌大国。当年在中国广泛搜集、最终编辑成一本《中国的儿歌》的美国人何德兰曾这样说过:“在中国,没有哪部文学作品,包括那些经典著作,能够像儿歌那样妇孺皆知。不管是识字的还是不识字的,不管是皇帝的孩子还是乞丐的孩子、城里的孩子还是乡下的孩子,他们全都能理解并传唱这些儿歌,这些儿歌在他们心中打下相同的印记。”
儿歌在中国为什么会有如此风景?大约是因为早先国人看到了“不登大雅之堂”的儿歌却有呼风唤雨、翻天覆地的力量,它的力量甚至被严重夸大了。《西游记·降魔篇》写各路降魔者五花八门的招数,但都比不上唐三藏掌握的三百首儿歌。唐三藏正是凭借这三百首富有魔力的儿歌,一路降魔,并将孙悟空制服于足下。中国儿歌史上出现的“荧惑说”,就是因为儿歌功能的阐释者将儿歌隐形力量神秘化的结果。他们将儿歌看成了历史颠覆、变迁的预言、谶语。“帝非帝,王非王,千乘百骑走北邙。”一首洛阳童谣,后来居然变成了事实,于是人们感到了儿歌具有令人不安的“荧惑性”。其实,那首儿歌呈现出来的情景或许是人们根据种种腐败堕落之现象推演出来的必然情景,而不是唯心主义的天意预言和谶语。
但儿歌的能量确实不可小觑。那些口口相传的儿歌经典,“一儿习之,可为诸儿流布;童时习之,可为终身体认”。许多人对童年吟唱儿歌的记忆都充满了无限深情、诗意与透彻的见解。林海音在《在儿歌中长大》中说,语言的学习、常识的增进、性情的陶冶、道德伦理的灌输,这一切都是从“儿歌中得到的”,“因此我们敢说,中国儿歌就是一部中国的儿童语意学、儿童心理学、儿童教育学、儿童伦理学、儿童文学。”1918年,北京大学号召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搜集歌谣,也正是基于对包括童谣(儿歌)在内的歌谣能量的高度估价。许多作家学者都参与了这个今天看来有点“小题大做”的计划,鲁迅也是形成这一计划的重要建议者。对于这次声势浩大的搜集歌谣之运动,我们至今实际上未能给出恰切的起因分析和意义判定。北大知识分子何以对作为“民间文学”的歌谣如此在意与推崇?那是因为这些包括童谣(儿歌)在内的歌谣对人生的影响是深刻的,是与血液和灵魂相关的生命元素。同时,他们理性地看到了这些歌谣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所发挥出的重大作用。我想,促使他们发动如此大规模的活动,可能与他们童年吟唱童谣(儿歌)、以及这些童谣(儿歌)是如何影响了他们的成长有关——这或许是直接原因。
在图书还没有出现,或还没有成为普及性阅读媒介之前,口口相传的童谣是十分重要的社会学、伦理学、美学、科学的无形的教科书。它不是通过看,而是通过念、吟唱乃至喊叫而流传四方、深入人心,而永世不忘。
所谓“童蒙”,是说儿童呱呱问世,其心灵的原始状态正如英国哲学家洛克描述的那样,犹如一块白板,是无知无识的,需要“启蒙”,于是逐步有了“蒙学”“蒙养教育”。早在中国古代就已经认识到了蒙学、蒙养的意义:只有在生命“幼稚阶段”时就打下良好的精神基础,才有可能在后来成为健康有力的生命,行进在合理而美好的人生道路上。那么,什么才是蒙学的“教材”呢?毫无疑问,儿歌是其中一项很好的选择。儿歌与儿童具有与生俱来的语言节奏感和乐感,最初,儿童也许并不理解那首儿歌的含义,但却能很快记住,然后再慢慢理解其中的含义。逐步完善的“蒙学”,将儿歌从政治附庸的位置逐步移至道德素养教育,而到了后来,它的主题领域和形式也日益扩大和变化,“生活歌”“知识歌”“节令歌”“劳动歌”“数数歌”“催眠歌”“谜语歌”“颠倒歌”,不一而足。但其意义却因为这一切皆为“小儿之歌”而非常容易被忽略。
儿歌是与儿童的游戏精神最为契合的一种文体。“游戏精神”是哲学、心理学、精神现象学的发现:从“人类幼崽”的最初行为中,他们发现人天生具有游戏的欲望。今天,相关理论体系已经建立并趋于完善,“游戏精神”已经成为一个现代“蒙学”的基本话题。而此时我们发现,儿歌是所有蒙学“教材”中最能与这一精神和谐共振的。现代儿歌理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它开始讲究“文学性”,作为儿童文学的一种,其主题领域更加广泛,也更加深邃。哲学开始进入儿歌,许多作家将审美功能也视为儿歌的功能。比如,“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叶圣陶《小小的船》)这样的儿歌,显然是作家带着审美意识而写就的。
儿歌开始带入诗性,与儿童诗的界限变得模糊,这些变化使得“蒙学”更具质量,也使得现在的儿歌更像诗。如,“小板凳,真听话,跟我一起等妈妈,妈妈下班回来了,我请妈妈快坐下。”“萤火虫!萤火虫!你是一个小灯笼,晚上照我去游戏,太阳一出影无踪。”这样的儿歌是诗人的创作,这些变化也提升了儿歌的境界与质量。
在图书丰富、网络发达的新时代,儿歌在儿童的吟唱和阅读空间中已不太可能再像从前占有那么大的比重了,但我们依然可以将它看成十分重要的蒙学、蒙养文体。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和出版人需要对儿歌在新时代的意义作出理性阐释,以告知相关推广部门重视儿歌的创作与传播。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缺少足够的高质量的儿歌。从前的“群相习,代相传”的儿歌,是“不知作者所自”的民间创作,在传播中不断被修正完善,一首意思相近的儿歌可能有很多的地方版本和时间版本。而现在的儿歌是由有名有姓的作家们创作出来的,“民间创作”几乎销声匿迹了。当我们的创作不能满足儿童对儿歌的需求时,当我们不能足够重视儿歌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意义时,儿歌的“民间创作”就会自然开始。同时,除了作家们需要提高自身的文学修养和创作能力外,还需要全社会对儿歌的意义有高度的认知。
(作者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