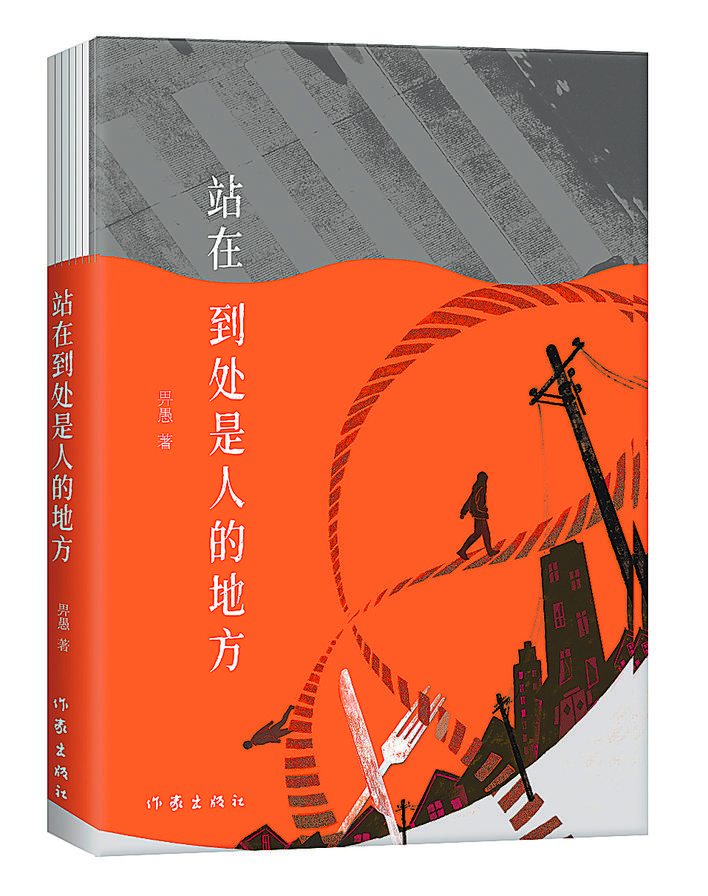玛格丽特
一
林红养花是受父亲影响。林老师在小学里教了30年语文,工作中没见多大建树,却在喝酒与养花上面出了名。他是握着半杯五加皮,一头栽在院子的花丛中心肌梗死的。那一年,林红25岁,噩耗传来时正跟志平在新房里忙。新婚在即,小两口几乎每个黄昏都在他们的新房里收拾。可是父亲死了,一句话都没留下。等他俩赶到医院,父亲已经直挺挺地躺在太平间里。林红一下子回想起坐在他腿上背诵唐诗的童年时光。
婚礼一直被推迟到第二年春天。就在她出嫁的前一天晚上,母亲忽然带了个男人回来。那人林红认识,小学里的副校长,姓刘。父亲的追悼会就是由他主持的。可一见他进屋那样子,林红就明白了,连客套话都不想说,起身就往自己屋里去。母亲叫住她,让她陪刘伯伯说会儿话。林红停了停,转身看着母亲。母亲脸上有点挂不住了,却硬要挤出一点微笑来。倒是那个副校长很坦然,在沙发里坐下来,说他听说林红要出嫁了,是来道个贺、探望探望的。母亲赶紧接过话茬,让女儿还不谢谢刘伯伯。林红没理她,把目光转到副校长脸上,盯着他看,却仍然没有一丝表情。副校长坐不住了,站起来用力咳了咳后,说我还是先回去吧,看来来得不是时候啊。母亲慌忙挽留,留不住,就一直送到门外,嘀嘀咕咕说了些什么,林红听不清,也不想听,扭头进了自己房间。
这个晚上林红没睡好,胡思乱想了一整夜。
第二天,志平用一部加长的婚车把她接走。在一片爆竹声中,林红隔着车窗回望,大家都在那里胡乱地向她挥手,这些人中间没有她的母亲。林红的母亲这一天几乎没跟女儿说过话,她对每个人报以浅淡的微笑,可这笑容里没有女儿出嫁的喜悦,就像父亲出殡那天,她的眼泪中没有悲伤一样。
婚车转过一幢楼时,林红猛然想起来,说,我还有东西要拿。车子戛然而止。林红想了想,又说,还是明天吧。她看着丈夫,明天我们去把院子里的花搬回去。
志平笑了笑,没说话,拉起她的一只手,捏在掌心里。林红想起来了,明天他们要去海南度蜜月,不禁又回过头去,再次看着车窗外那些渐行渐远的风景。
林红的蜜月十分短暂,原因是志平工作忙。他是工程学院的讲师,讲师跟教授不一样,每天都有好几堂课等着他。不过,他向林红保证,等放了暑假一起去西藏,再像模像样地度上一回蜜月。林红点了点头,枕在他胸口,一只耳朵听着他的心跳,一只耳朵听着窗外海浪席卷沙滩的声音。那是他们在海南的最后一夜。小夫妻俩回来后就回了趟娘家,这是沿袭了千百年的老规矩,叫回门。但是,林红刚进门就傻眼了,她站在院子里,那么多的花一盆都不在了,院子里新浇的水泥地早已干透,显得宽敞而洁净。母亲在她身后淡淡地说老刘有哮喘,他对花粉过敏。母亲还说他们已经定下了,旅游结婚,去的目的地也是海南。林红只是惦记那些花。太阳当头照耀着,她问母亲:你们把我的花弄哪儿去了?
卖了。母亲说着,去屋里拉开抽屉,取出一个信封塞给女儿,卖花的钱在这儿。她强调说,这是老刘的意思,钱,我们一分不要。
林红捏着钱,一句话都没有。
回门这顿午饭吃得极其沉闷,吃完了,她一拉志平,说,我们该走了。
志平一直是笑眯眯的,保持着新郎官的愉悦。他在走出很远后,对林红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管她呢。林红没理他,挎着他的胳膊,一路上始终低着脑袋。志平笑了笑,又说,只争朝夕啊,看来你妈是个急性子。
你有完没完了?林红平白无故地恼了,甩开他的胳膊,掉头去了育子弄的花鸟市场。她一个人在那条不长的街上来来回回地逛了好一阵,才挑了两盆蓬蒿菊抱回家,把它们移栽进阳台的花槽里。3年过去了,林红把育子弄里的植物一盆一盆搬回来,把阳台布置得像个花圃,而她的家就成了花园,一年四季都开满了鲜花。但林红还是更喜欢蓬蒿菊,喜欢它们像野草一样在花槽里肆无忌惮地生长。那些白色的小花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每一片花瓣上都寓示着爱情。这是林红从一本书上看来的。书上还说蓬蒿菊在欧洲又叫玛格丽特,是16世纪一位瑞典公主的名字,它的花语是心中隐秘的爱情。
林红觉得那是胡说八道,是卖花人编出来骗钱的。但她喜欢看书是真的,还在跟志平谈恋爱那会儿,每个星期天,两人不是上书店,就是去图书馆。不过,志平现在没工夫看书了,他每天都忙得很,好像不是大学里的讲师,而在经营着一家公司,下了班基本上是往饭店里跑,吃完、喝完了还不算数,还得成群结队地去酒吧或是KTV里接着喝。为这,林红没少发脾气,最厉害的一回,她一个烟灰缸扔过去,把门口的玻璃屏风砸得粉碎。可是不管用,男人都把苦衷放在了肚子里,志平有一次喝多了,趴在卫生间的抽水马桶上才说了心里话:如今学问不在书本上,他要当副教授,他要当教授,他就得陪着这些人吆五喝六地在酒桌上混。吐完之后的志平,两眼空洞得像个垂死的病人。他把整条手臂搭到林红肩上,由衷地叹息:书中哪有黄金屋啊?
……
二
林红在大学里念的是金融,一毕业就进了银行,刚开始时分在理财部,可几次调整下来,一次不如一次,竟被派到下面的储蓄所去当了个出纳员。林红气愤,却也没办法,整天只能对着柜台前那块钢化玻璃,对着那些排队来存款、取款的男男女女,心里再怎么窝火,都得努力沉下一颗心来克制着。在这个岗位上是绝不能出差错的。林红每次都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可以错,就是数字不能错。银行里的数字就是钱。
但错误是难免的。银行的制度是“一日三碰库”,早、中、晚各一次,尤其是下班前那一次,光每个柜上的账“平”了还不算,一定要等到电脑里全省的账都“平”了,大家才可以下班,才可以回家。每天,储蓄所的大门一拉下,整个大厅里就剩下一片手指敲击键盘的声响,大家全神贯注,只知道埋头整理传票、核对流水。可是这天,主任一眼就发现林红出事了,透过办公室的玻璃幕墙看出去,她的脸红得好像一口闷下三两五粮液。主任是老柜员出身,不动声色,抓起电话把她叫进来,开门见山就问,差了多少?林红支支吾吾,说9万。主任听不见,说,你大声点,到底多了还是少了?
少。林红说少了9万。说着,她抬起头,眼睛里有两颗泪在晃晃悠悠。主任却无动于衷,让她先出去把账做平了再说。林红说,少了9万,你让我怎么平?
你不能把那9万先移到明天去?主任说,大家都等着你下班呢。
林红死心眼,问,那明天怎么办?
主任当然不会等明天,同事们一下班,他就让林红带着票据坐到监控室里,对着录像画面一个个地找,一张张地对。主任从外面买了两个盒饭来,说,不把这9万找出来,我们谁也别下班。
这天晚上,两个人忙了大半夜,最后还是主任从一张单子上看出名堂来。他把录像快进到一个时间上,定格,问林红,记不记得他?主任指着画面上的男人,他到底贷了多少?汇了多少?画面上的男人很模糊,就看得清他穿着一身运动服。林红摇了摇头,她的脑袋里这时候像灌满了糨糊。主任把单子往桌上一拍,说,人家贷10万,汇1万,你看你给他汇了多少?
林红看着单子,说,这怎么可能呢?
还不可能?主任瞪眼了,问她,那你的9万去哪儿了?
林红从单子上抬起头,脸上一下有了雨过天晴的表情。她说,我怎么可能多打一个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