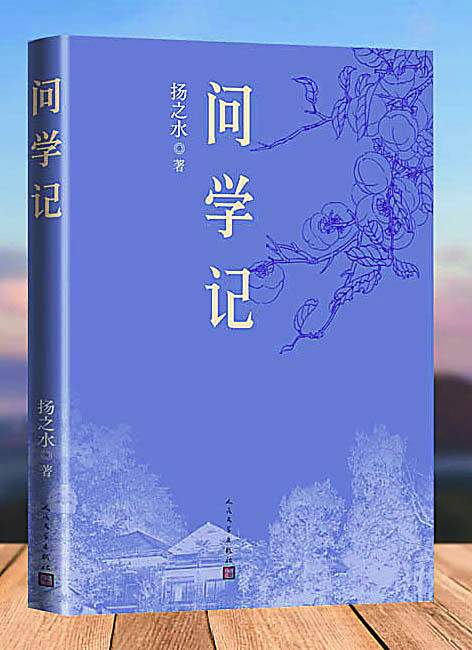□王运平
扬之水的《问学记》中那些文人文心文事,看似是简单的文字述说,读来确能使人心有所悟。“有事,弟子服其劳”,这句话无论何时读来都会让我的心为之一颤。扬之水是这句话之精神的践行者,她曾在日记中这样记述与徐梵澄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不过,稿子需要一一抄定。我表示愿意承担。”简单的两句话,把扬之水甘之如饴的弟子之劳尽述。
书中所记述的那些先生们,作者谓之“蔼然长者”,她通过《问学记》,让这些“蔼然长者”集中出场,以文人散淡轶事的方式给我们讲述着文心的构建和文人的自觉砥砺之路。以此,扬之水通过《问学记》将他们推为众人之先生。徐梵澄先生说:“我向不以灵感为然,学识方为第一,所谓厚积薄发是也。”这使读书人更知手不释卷乃拙之达途。说到谷林先生,扬之水有着这样的文字描述:“的确心无点尘,渣滓日去,散散淡淡瘦出的一剪清癯。”这心无点尘、渣滓日去,非日日向学、日日自新自醒难以建功。面对金性尧先生的女公子,扬之水“不敢再问是否还能读书,而心里知道,不能读书,对先生来说,生之乐趣也就没有了”。把读书视作人生之乐趣,是金性尧先生一家带给扬之水的印记,扬之水又把这种印记带给读者。说到“空如有”的金克木先生,扬之水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装备这样的头脑,要读多少书?若要靠买书来读,该需要多大的书房呢?”“这样的头脑”,是怎样的头脑呢?扬之水以未明之言言明了一种读书人所能达到的化境,使人读来心向往之。
“卫星总设计师胡海鹰说:‘热爱是一时的,剩下的全是责任;喜悦是一刻的,剩下的全是投入。’”扬之水说:“我认同这里的后一句。其实所有的投入,都是心甘情愿。”扬之水曾任读书杂志编辑长达10年,她尽于编辑之责,问学一众“蔼然长者”,问学书海,问学于心,终得所愿,个中辛劳可见一斑。岂止《读书》十年,观之《问学记》的代序和附录可知扬之水是一生问学,在这一点上,可为读书人表率。扬之水说:“80年代令人感念不置者,对我来说第一是对学历的宽容。”岂止那个年代,又岂止于学历这一个端口,肯于一生问学的扬之水获得的又岂止是宽容,她获得的是一种生命的风云之气。
《问学记》的阅读,一开始对我来说并不轻松,随着逐步的深入才渐次变得顺畅,其中的意趣和阅读的福祉也随之而来。我相信有这种感受的读者不止我一个,而问学之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世上没有一步白走的路,自然也没有一本白读的书。问学者,当读《问学记》。当下中国已进入全民阅读的时代,问学之路已是众生之路,从这个角度来说,扬之水的《问学记》已具备了普遍的推广意义。
(作者系中宣部版权管理局社会服务处一级调研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