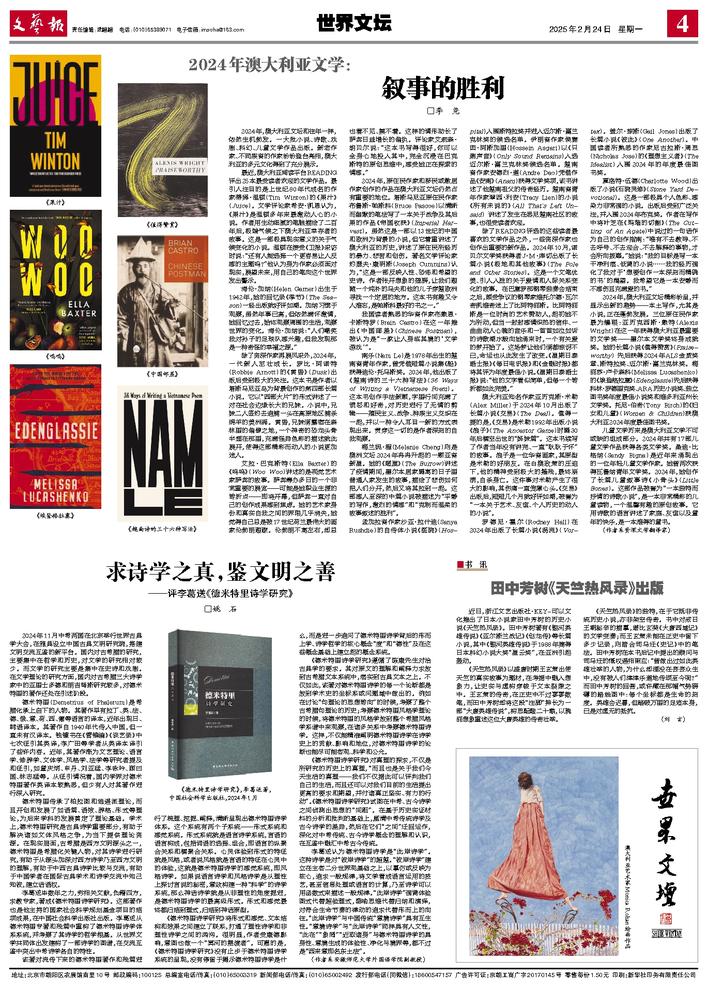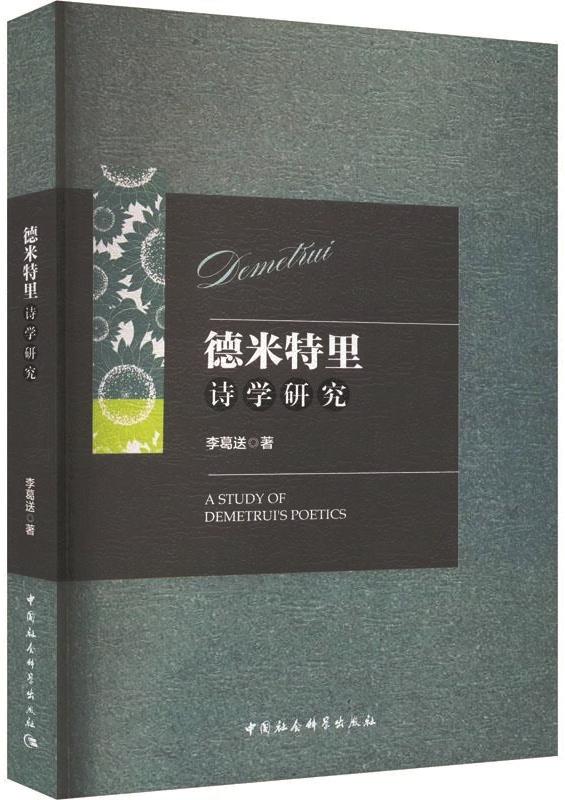□姚 石
2024年11月中希两国在北京举行世界古典学大会,在雅典设立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搭建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平台。国内对古希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和历史,对文学的研究相对较少。而文学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史诗和戏剧。在文学理论的研究方面,国内对古希腊三大诗学家中的亚里士多德和朗吉弩斯研究较多,对德米特里的著作还处在引述阶段。
德米特里(Demetrius of Phalerum)是希腊化承上启下的人物。其著作早有拉丁、英、法、德、俄、意、荷、西、葡等语言的译本,近年出现日、韩语译本。其著作自1940年代传入中国,但一直未有汉译本。钱锺书在《管锥编》《谈艺录》中七次征引其英译,李广田等学者从英译本译引了些许内容。近年,其著作渐为文艺理论、语言学、修辞学、文体学、风格学、法学等研究者提及和征引,如童庆炳、申丹、刘亚猛、李咏吟、顾曰国、林志猛等。从征引情况看,国内学界对德米特里著作英译本较熟悉,但少有人对其著作进行深入研究。
德米特里传承了柏拉图和逍遥派理论,而且开创和发展了如语篇、语效、辞格、形式等理论,为后来学科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学术上,德米特里研究是古典诗学重要部分,有助于解决诸如文体风格之争,为当下提供理论资源。在现实层面,古希腊是西方文明源头之一,德米特里是希腊化关键人物,对其诗学进行研究,有助于从源头加深对西方诗学乃至西方文明的理解,有助于中西古典诗学比较与交流,有助于中国学者在国际古典学术和诗学交流中知己知彼,建立话语权。
李葛送毕数年之力,穷相关文献,负籍四方,求教专家,著成《德米特里诗学研究》。这部著作也是他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李葛送从德米特里专著和残篇中重构了德米特里诗学体系系统,并考察了其诗学的哲学根基。从世界文学共同体出发建构了一部诗学的图谱,在交流互鉴中突出中希诗学各自的特性。
该著对流传下来的德米特里著作和残篇进行了梳理、挖掘、阐释,清晰呈现出德米特里诗学体系。这个系统有两个子系统——形式系统和感觉系统。形式系统就是语言诗学系统,言语的语言构成,包括词语的选择、组合,即语言的纵聚合关系和横聚合关系。心灵体验到形式的特征就是风格,或者说风格就是言语的特征在心灵中的体验,这就是德米特里诗学的感觉系统,即风格诗学。如果说语言诗学和风格诗学是从理性上探讨言说的秘密,意欲构建一种“科学”的诗学系统,那么神话诗学就是从非理性的角度掘进,是德米特里诗学的最高级形式。形式和感觉最终都归结到理式,归结到神话原型。
《德米特里诗学研究》将形式和感觉、文本结构和效果之间建立了联系,打通了理性诗学和非理性诗学之间的鸿沟。很明显,作者受康德影响,意图也做一个“冥河的摆渡者”。可嘉的是,《德米特里诗学研究》没有止步于德米特里诗学系统的呈现,没有停留于揭示德米特里诗学是什么,而是进一步追问了德米特里诗学背后的形而上学、诗学哲学的核心概念“度”和“德性”及在这些概念基础上建立起的概念系统。
《德米特里诗学研究》遵循了陈康先生对治古典学的要求。其对原文的理解和阐释力求放到古希腊文本系统中,落实到古典文本之上。不仅如此,该著对德米特里诗学的每一个论断都是放到学术史的坐标系或问题域中做出的。例如在讨论“句理论的思想转向”的时候,考察了整个古希腊句理论的历史;考察德米特里风格学理论的时候,将德米特里的风格学放到整个希腊风格学系谱中来观察,在诸多关系中考察德米特里诗学。这样,不仅能精准阐明德米特里诗学在诗学史上的贡献、影响和地位,对德米特里诗学的论断也能尽可能客观、科学和公允。
《德米特里诗学研究》对真理的探求,不仅是所研究的历史上的真理,“而且也是关于我们今天生活的真理——我们不仅据此可以评判我们自己的生活,而且还可以对我们目前的生活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期望,并付诸真正坚实、有力的行动”。《德米特里诗学研究》试图在中希、古今诗学之间侦测出思想的“间距”。在基于历史实证材料的分析和批判的基础上,厘清中希传统诗学及古今诗学的差异,然后在它们“之间”迂回运作,深化对中希传统、古今诗学概念的理解和认识,在互鉴中融汇中希古今传统。
李葛送认为德米特里诗学是“此岸诗学”。这种诗学是对“彼岸诗学”的超越。“彼岸诗学”建立在主客二分世界观基础之上,以摹仿或反映为核心,追求一般规律,将文学看成语言运用的技艺,甚至信息处理或语言的计算,乃至诗学可以用函数式来描述一般规律。“此岸诗学”强调体验图式代替超验理式,隐喻思维代替归纳和演绎,对符合生命节奏的律动的追求代替形而上的向往。“此岸诗学”与中国传统“意境诗学”具有互生性。“意境诗学”与“此岸诗学”同样具有人文性,“此在”“象罔”“近取诸身”与德米特里诗学的具身性、意境生成的体验性、净化与境界等,都不过是“西来意即名东土法”。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