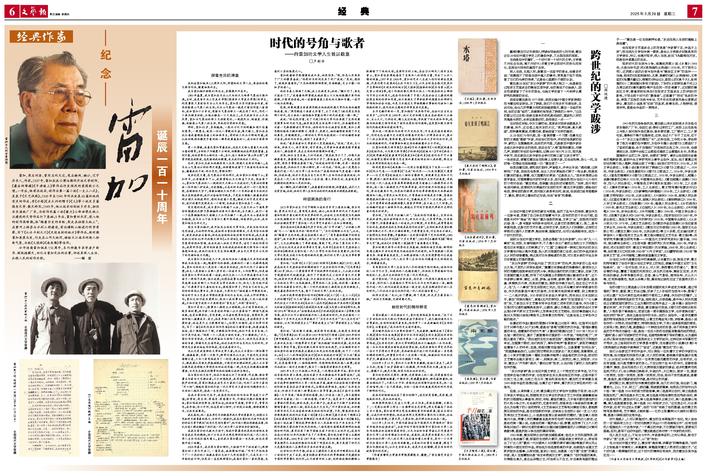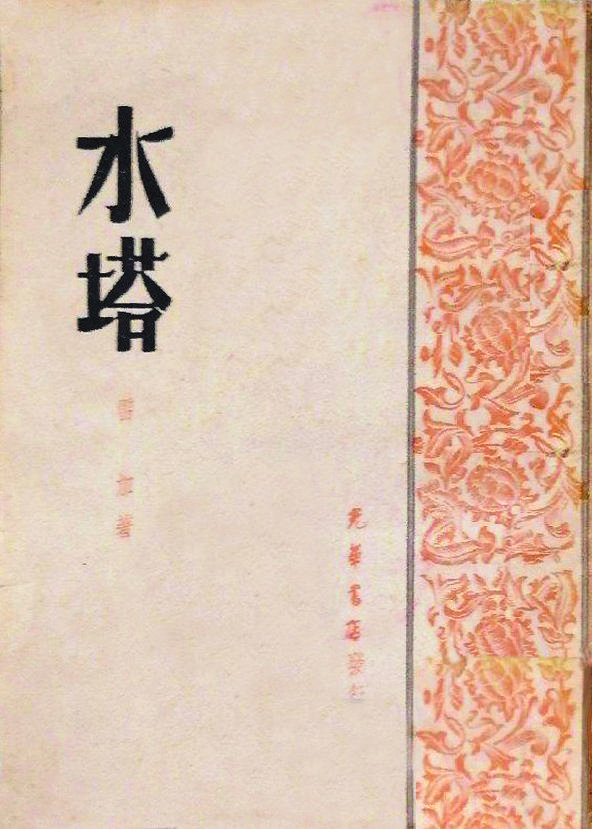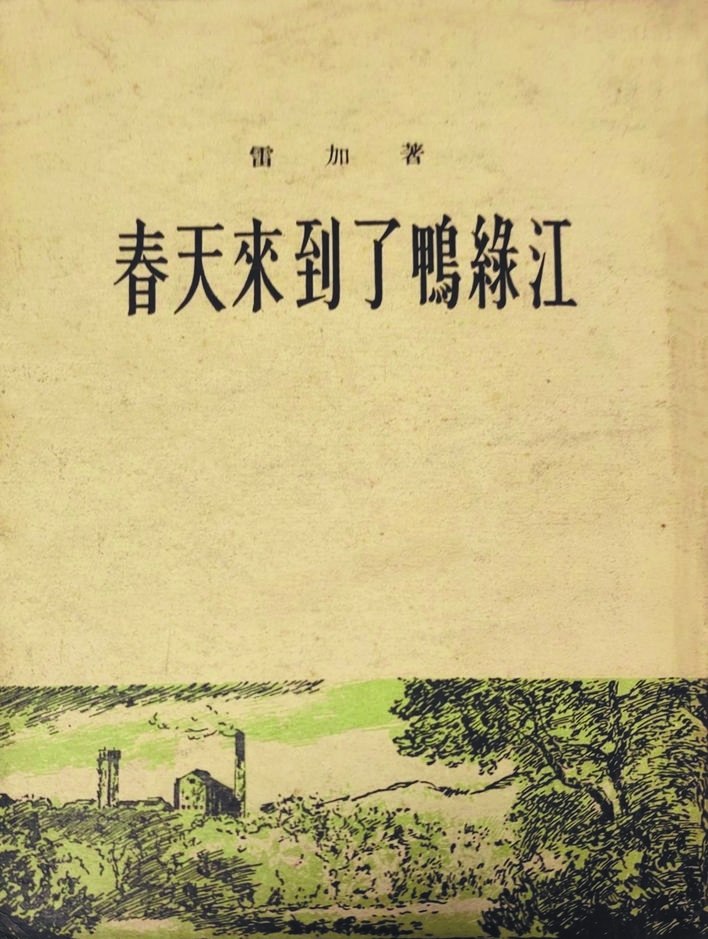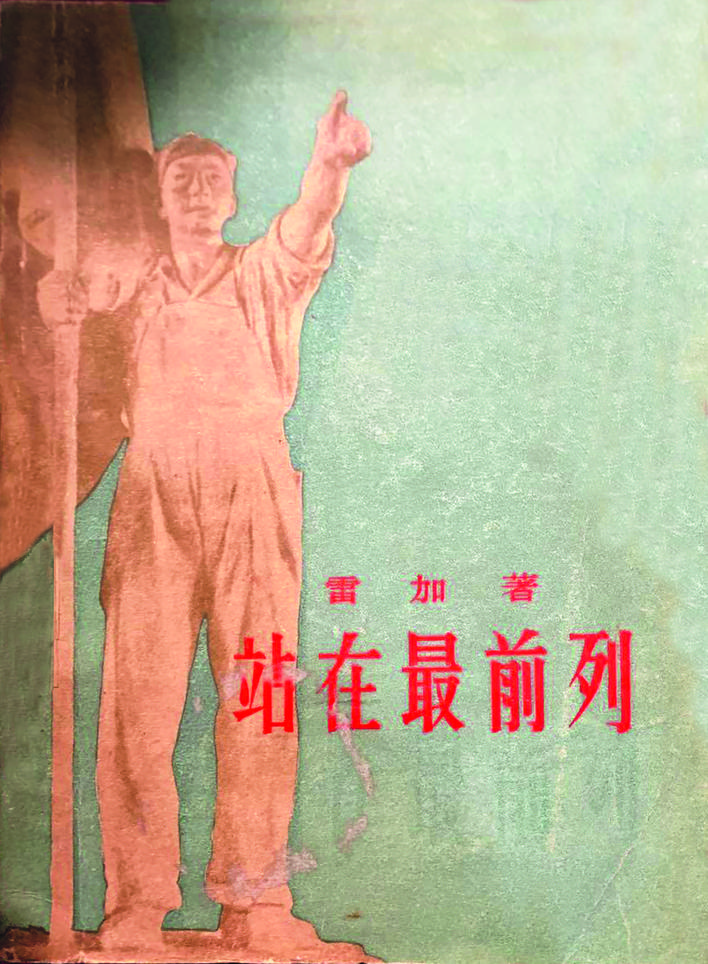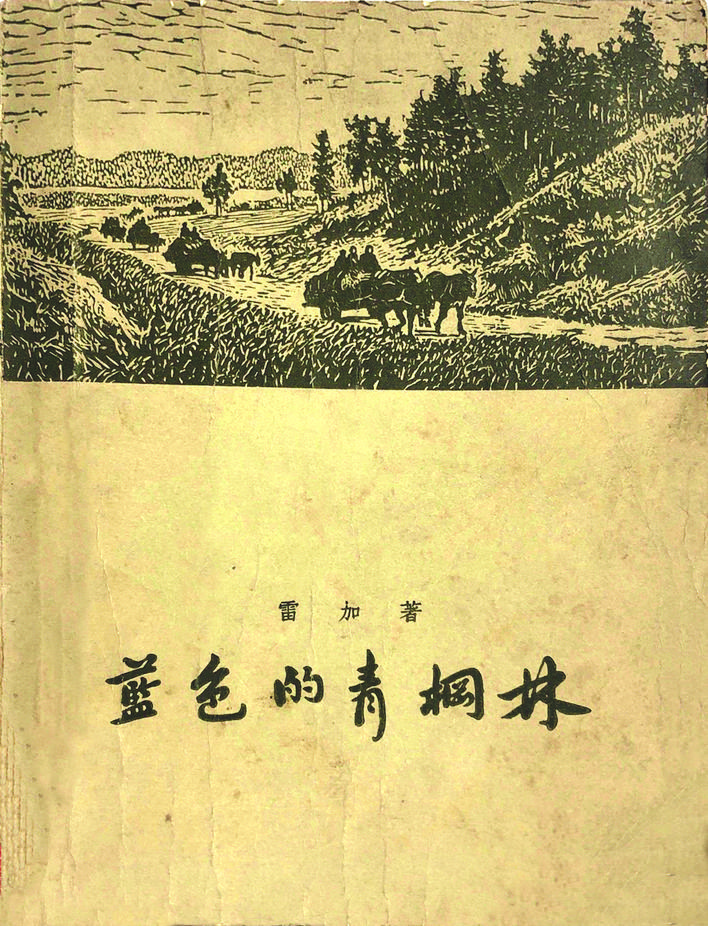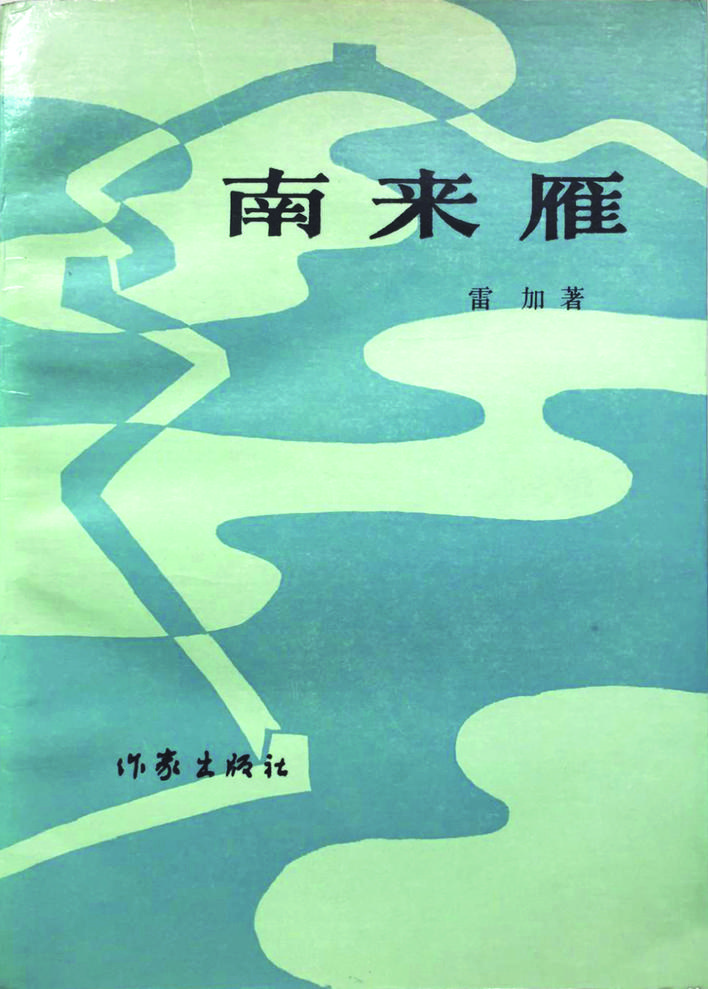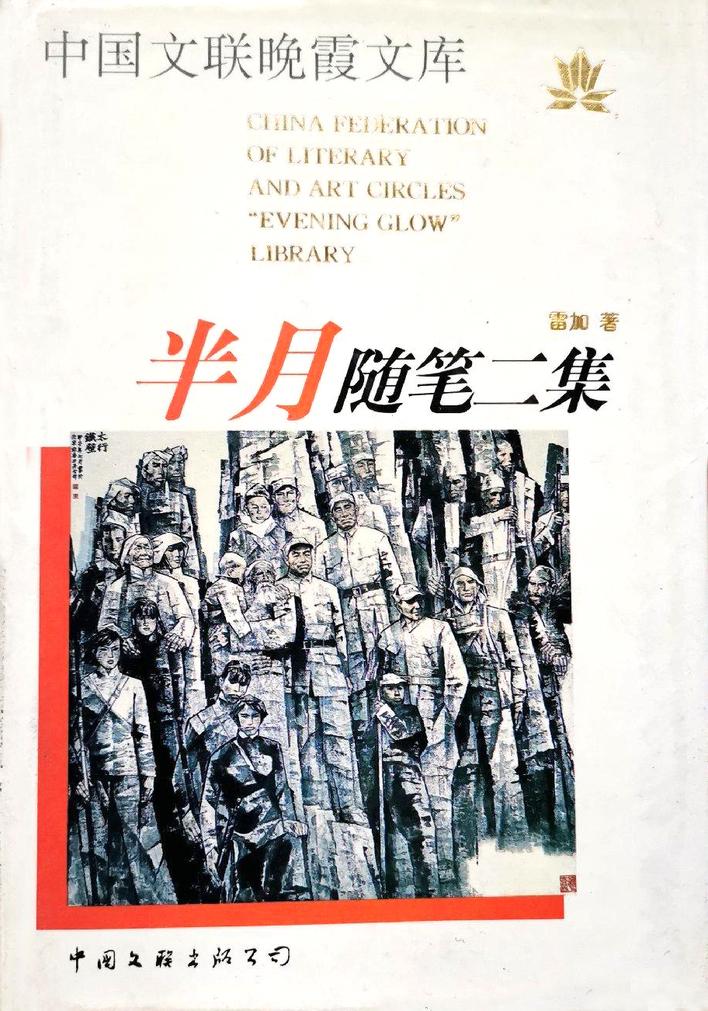□卢新华
探索生活的诗意
在纪念雷加诞辰110周年之际,仰望他的文学人生,再读他的散文特写作品,敬意油然而生。
我与雷加相识转眼45年过去,其情境历历在目。
1980年盛夏,我与雷加在长白山天池的天文峰旁气象站不期而遇。当时,我是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学生,利用暑假只身前往长白山天池写生。雷加是北京作家协会作家,前来体验高山气象人的生活。长白山气象站一般是不留任何客人食宿的,我和雷加十分幸运,有缘与气象站职工一起生活了四天,同吃一个高压锅里的饭,头挨头睡在一个大热炕上。白天我画长白山天池风景,雷加与气象站的职工交谈做笔记,一起观风云、测温度、抄数据,体验高山气象人的生活,寻找创作素材和灵感。
那时,雷加65岁,身材魁梧,一脸北方汉子的刚毅和阅尽沧桑的宽厚,一眼望去,就是一位让人尊敬的长者。每天晚上,雷加坐在炕头看我整理挂在墙上的油画写生,有时他又低头不停地写着。我从他的眼神和微笑中看到他一颗寻找真善美的心,我与他不再有陌生感。
有一天傍晚,我看见雷加穿着皮袄,站在天文峰山顶看天池云起云落的情景。当时的夕阳晚霞十分绚丽,他默默地站在那里观望着,直到日落,他的身影与山峰化为一体。至今,这个画面如“高山仰止图”,常常浮现在我眼前,总是触动我的敬意,成为我对他的永久回忆。
也许,雷加认为我和他都是深入生活、拥抱大自然的同路人。在长白山气象站分别的那天清晨,他特意给我留下了他家的电话和地址,握着我的手说:回北京见,常联系啊!
说来也是天意,在气象站分别的那天,我和雷加分两路下山。雷加年长,从原路乘车下山,我要冒险从天文峰直下天池,然后再下山。雷加和气象站的人一起赶到天文峰山口为我送行,气象站还特意派一位年轻人护送我,为我领路。正在此时此刻,我们一行人忽然发现,在晴朗的天空下,清澈如镜的天池中有一个东西拉着长长的划水线正在快速移动。我们兴奋地惊呼起来,于是我与领路人踩着滚动的碎石朝天池快速滑行,想到池边看个究竟。据说天池中是没有生物的,我们的意外发现成为一个新闻,也把我与雷加连在了一起。
更没想到的是,我与雷加分两路下山后,又在天池山下温泉旁临时搭建的木愣子席棚接待站再次不期而遇。当天晚上,我们一老一少在席棚接待站大通铺上又头对头睡了一夜。在长白山顶我和雷加相遇,在长白山下我与雷加又意外再相逢,倍感亲切。从此,我和雷加结为忘年之交。
因为与雷加相识,我开始关注他的文学作品,并成为他作品的忠实读者。无论何时何地,我始终与雷加保持联系,不是写信与他联系,就是找机会去看他。他也总会把他出版的新书送给我。我尤其喜欢他20世纪60年代的散文特写《山水诗话》,语言的画面感很强,文思富有诗性和哲理,我由此进入他的文学世界,读完了他的所有作品。我有时写信,有时到他家里与他谈我读他的散文特写和小说的感想和体会,谈他们延安文艺生活的趣事,谈当代文学艺术以及时下的思潮和焦点问题。
我与雷加交往的这几十年,他的作品和人格魅力及共同的话题将我与他连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跟他们一家人也都熟悉起来。雷加与他的夫人是延安一起过来的战友,他们之间十分融洽亲密。他夫人是原轻工业部人劳司的一位老司长,工作很繁忙,但是她总是雷加文学作品的第一读者。他们夫妇二人几乎将我看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给予关照,指点迷津。记得在我事业选择的关键时刻,究竟是选择去政府部门工作还是去学术机构工作,他夫人坚定地对我说:“不要离开自己喜欢的专业。要向雷加学习,守住自己的专业。回到你的母校从事专业,努力奋进,大有作为!”她说着立即拿起电话,给当时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党委书记打去电话,让我立即回学院工作。雷加夫妇对我关爱有加,既关心我的事业发展,又关心我的家庭。不知不觉中我改口不再称雷加“雷先生”,而称“雷伯伯”。
雷加平易近人,做事为人都是从正面做起,从不说负面的话,不做负面的事。他对家人和身边的年轻人从不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地说教,总是和蔼亲切,言传身教,以长者的宽厚和包容,因势利导,帮助年轻人健康成长、成才。他是年轻人的良师益友,身边有很多文学爱好者,他总是尽全力提携年轻人。记得大四期间,我不知学问深浅,写了一篇《论民间美术创作思维》的论文请雷加看。他看后诚恳地说,这个领域他不了解,不敢做任何评说。他似乎是自言自语,又似乎是对我说:“倒有一个人是这方面的专家,可以请教他。”不久,雷加写信告诉我,已将我那篇论文转给了沈从文,说沈先生是这方面的专家,特请沈先生指导我。他还为我约好去见沈从文的时间,并将沈先生家的地址写好给我,这让我感动不已。
沈从文是我崇拜的文学和史学大家。沈从文与雷加一样和蔼可亲,循循善诱,没有一点架子。拜学问道沈从文后,可能沈先生怕我理解不透,又专门亲笔给我写了一封信,教我如何做学问、如何写论文,教我要从实物史料基础做起,不做空洞的理论研究。这又正与雷加教导我怎样做文学研究和评论的思路一样。沈先生的教诲如醍醐灌顶,与沈先生相见的情景和他的指教让我终生难忘。
在与雷加的交往中,他还介绍我认识了刘绍棠、邓友梅、理由等著名作家和文艺理论家。今天回想起来,我深感幸运,在我创作研究起步的时候,是雷加领我走进艺术大家的门栏,吃到了名师大家的“开口奶”,领略到雷加他们这一代文学艺术大家的创作精神和为人处世的人格风范,使我一生受用不尽。
在我与雷加的交往中,我感受到他的创作和治学态度十分严谨。他常说,有生活、有感受、有感情才写,对理论问题不做随意评述。雷加给我回信简洁,惜字如金。他谈话节奏慢,言辞不多,常常沉思。我年轻,信口开河,他总是耐心倾听,不时校正话题,理顺逻辑关系,让我受益匪浅。
我也感到,他一直在用艺术的敏感寻找文学的青春活力,他想让文思始终充满青春的张力,与时代一起前行。我在与雷加的交谈中和我写的评论文章中提到“延安文艺创作意识”,他对这个提法很敏感在意,他认为这个提法概括了他们这一代人的文学人生命运和价值归宿。
在我与雷加的无数次交谈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面向未来和自我反思的精神。他十分关注历史将怎样评价他们这一代人的文学人生和作品价值及意义。直到我与雷加最后一次见面,他也没有绕开这个话题。
2008年春天,我没有与雷加预约,又轻轻叩开了他的家门。照顾雷加的小芳打开房门,一看是我,她热情地呼喊:“爷爷!卢叔叔来了!”一个农村的小姑娘在雷加夫妇十几年的培养下,已成长为一个年轻的会计师,但是还一直在照顾雷加。我感叹雷加一家的厚德,也感叹小芳的报恩之心。
雷加扶着助步架慢慢迎我而来,他很惊异:“咦,你怎么突然来了?”又好像责备我:“你有好长时间没来了吧?”我说:“是的,想你了,就跑来看看你。”只见他两眼炯炯有神,思维敏捷,完全不像一位94岁的老人。
他的书桌上堆满了文稿,床上也满是书。他说:“腿不行了,再也不能出门了。”我看着他那曾经走遍祖国山川大地的铁腿不再听他使唤,不禁有些伤感。他一边整理着桌上杂乱的文稿和书籍,一边开心地与我聊着。
忽然,他拿起著名画家周思聪为他抗战时期文学作品画的插图给我看,说:“周思聪这个画家太厉害了,太了不起了!她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怎么画的人物性格和穿戴与那个时代的感觉一模一样。”
我说:“你也很厉害,也了不起!你的文学作品再现了生活的真实情景和时代的气息。她虽然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但画插图的艺术家一定都要精读文学作品,读你的作品让她身临其境,再加上周思聪的绘画天赋和理解力、想象力、表现力,她的插图就再现了历史的真实,并超越现实。一部好的文学作品能遇到一个好的插图画家不容易。你的作品幸运,遇到了名家高手。”
他说:“看来画家和文学家的心灵是相通的。”我说:“是的,文心诗画,诗画文心,画中有诗,诗中有画。文学家和画家都是探寻真善美的人,都在探寻、表达生活的终极情境和诗意。”
突然,他似自言自语,又似对我说:“现在我写不了了,但每天我都要看书,要整理文稿。我的时间不多了,要准备走了。不想走,也得走啊,有很多事情我要做了结。”他说这话时很平静,没有一丝忧伤感和焦虑,但他似乎又难以释怀,再一次问我:“你说,后人究竟怎么看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学人生和作品?”我感到他语气里透着一丝孤独,但我知道,他并不是在为自己的文学人生和作品价值找说法,而是在为一代人的文学道路和人生价值、意义寻找定论,或者说在寻找精神的观照和心灵的归宿。
这一瞬间,我们都沉默了。我看着雷加的眼神,他望着我,我们久久没有言语。此刻,他的文学人生和作品的时代画卷再次涌现在我眼前。
吟颂民族的前行
1915年雷加出生于辽宁鸭绿江边的丹东市三道浪头镇,原名刘涤,曾用名刘天达,曾用笔名赫戏、赫公。他的青年时代处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冲突和变革的时代,社会的主流思想是为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而斗争,为创建新中国的理想而奋斗。这一变革时代的社会潮流贯穿了雷加这一代文学艺术家的人生和全部理想。
雷加在他的《南来雁》代序中写到,他“不早不晚”,“正好搭上那趟‘九一八’驶向关内的‘特别列车’”,“为打到鸭绿江而生”。从此,他“踏着历史的车轮,奔走在祖国大地上”,“肩负着祖国赋予的神圣使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从卢沟桥走向全国,又从全国走向延安”,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革命道路,拿起了笔,开始了漫长的文学人生。作为从延安走出来的革命文艺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成为雷加这一代人文学艺术创作的自觉意识,他们的文学之笔成为战斗和思想的锐利武器,他们的文学人生成为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雷加说:“从特写《土门》(1939)到特写《英雄之路》(1979),就是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指引下走过的创作历程。”(《浅草集》第140页)他从一个爱国青年学子到战争年代的战士,又从战士到新中国建设时代的建设者,经历了中国现代史上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他是时代变革的参与者,历史转折的见证人,民族忧患和生死存亡与他的文学人生休戚相关,贯穿他的人生主线,他的每一篇散文特写作品都紧扣时代,每一个时代的转折又都是他生活的新起点,散发着浓厚的时代气息,留下了他的文学人生的足迹。
从抗日战争时期雷加创作的《鸭绿江》《土门》《一支三八式》《五大洲的帽子》《“女儿坟”最后一代》等作品,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末的《乌拉尔人在沉思》《拖拉机开来的那天》《新唐屯的诞生》《植物的话》《火烧林》《白马雪山》《玉龙雪山诗话》等作品,再到1976年“拨乱反正”后结集出版的《沙的游戏》《边城和人》等散文特写集,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经历的人生轨迹和时代,而且还看到一个跨越六十多年历史的文学家经历了“为艺术而艺术”“为人生而艺术”的转折,以及“批判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观念的转变。
雷加说:“我的散文道路,就是特写的道路,也就是生活的道路。”(《浅草集》140页)从雷加1937年创作《平津道上》到1945年创作《黄河晚歌》,这八年间是抗战艰苦岁月。在这一背景下,散文特写形式再次成为这一时期革命文艺家“短兵相接”的锐利武器,成为民族解放斗争的号角。雷加的散文特写创作由此起步,以白描特写的手法和质朴的语言风格表达着战士和民众的思想感情,记下了一代风云。如《三个人的阵地》《敌后行》《妇女抗战进行曲》《“女儿坟”最后一代》《路》《沉默的黑怀德》等代表作品,既是弥漫着前线硝烟的特写,也是感情丰富、人物性格鲜明、思想倾向强烈的感人故事。这些作品犹如一面历史的镜子,展示了一幅富有诗意的历史图景。
1945年8月15日祖国山河光复,人民解放战争开始,雷加告别延安窑洞和黄土高原,赴他的家乡东北根据地丹东接管造纸厂。这一时期,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恢复生产、支援前线的工作中。抗日战争时期鲜明而又单一的民族矛盾,被新旧社会体制交替时期的阶级和复杂社会矛盾所取代。当解放战争结束,造纸厂生活成为过去,吟颂不尽的新人新事在他心里孕育着。他在《不能对生活骄傲》一文中写道:“集体劳动的感情,把人们连在一起了。伟大感情的洪流冲击着这一切……新的感情,不断产生,这是由于人类酷爱新生事物而得来的。新的品质,也不断产生,这是由于不断产生新的感情哺育着它。新的人物,因此也在天天生长。”对于雷加来说,此时散文特写形式已无法容纳和满足他的创作欲望,于是,情感洪流和生活源泉激发他创作出长篇小说《潜力》三部曲(《春天来到了鸭绿江》《站在最前列》《蓝色的青棡林》)和具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鳝鱼》。这些小说反映了解放战争时期东北人民在新旧生产关系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交替过程中的风风雨雨,人物思想和感情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时代性,真实记录了新中国诞生前夕初创工业的历史。这些作品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产生了广泛影响,雷加成为新中国工业题材的代表作家。1946年至1957年这一时期,雷加的散文特写和小说的审美境界已与抗战时期的作品有了明显的区别,集中表现了时代交叉发展阶段的人生境界和多层次的审美主题。
20世纪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生活呼唤雷加从长篇小说创作中走了出来,投身到根治黄河的水利资源梯级开发建设和中国科学考察队的行列。从九曲黄河的上游,到西南边陲的横断山脉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黄河水利工地,在金沙江畔及人迹罕至的雪山,雷加身临其境地感受了自然和人的诗性力量,写出了山水人情的诗篇。1957年至1966年,雷加的艺术人生进入创作的黄金发展期,代表作有已成集的《从冰斗到大川》,以及当时在各报刊发表而产生影响的《足迹未到的地方》《火烧林》《植物的话》《白马雪山》《玉龙雪山诗话》等。这个阶段的散文特写比他上一阶段在他的全部创作中所占比例更大。这些作品记载了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征服自然的创举和思考。他不再满足于革命战争时期需求的那种文学倾向和社会功能,而是力求通过文学语境揭示事物的内涵和人物性格的特点,使作品的主题向多种审美层次发展。
当历史翻开新的一页,雷加相信“未来给予的,总会比过去失去的更多”。1976年至1988年,他以充沛的精力奔走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名山大川,几回延安,踏上走过的路,寻找留下的足迹和年华。这期间他的散文特写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创作高峰。这是雷加散文特写创作风格成熟和收获的季节。
雷加这一时期的作品有对历史的反思,对自我价值的重新认识,同时也包含着历史与现实的情感冲突给人们带来的启示,展示了人的主体诗性,富有新意。雷加这期间有如此之多的作品问世,是与他拥抱新时代、对新事物和新生活的敏锐意识分不开的。
从雷加的散文特写集《火烧林》中的北疆特写《心的歌》《向着未来》这组作品,以及散文特写集《沙的游戏》《边城与人》中的《游击二月》《战争插曲》《首渡黄河》《高度》和《窑洞里》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他触景生情的诗意文思自然而真实地唱出他心底的歌,将过去与未来用诗性的追忆连在一起。
特别是雷加的《南来雁——忆烈士张露萍》《为了未来——记丁玲》《泥土气息——忆柳青》《“忘我”的沉思——忆吴伯箫》《大漠雷声——忆艾思奇》这组追忆人物的肖像特写,再现真实生活和平凡小事,提炼人物所具有的个性特征,站在审视历史时代的角度,寻找他们这一代人在追求崇高革命理想的漫长道路上人格境界的不同特征。这一组人物都是无产阶级革命者,他们的经历和性格各不相同,命运也截然不同,但是他们都有共同的革命理想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和人格。不管风云如何变幻,不管奉献与回报是否平衡,崇高的理想使他们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坚毅地走完了人生之路。这一代人为中国革命的奉献精神像大漠雷声那样,在大地上久久回荡。无论谁翻开这些人物特写作品,都能从中听到中国现代革命历史那沉重而悠长的回声。
雷加说,“生活是不会骗人的”,“在我的创作道路上,生活永远是我的老师。这位老师隐而不见,却无处不在,又异常严格,它虽然乐于赐予,但需要真诚无二的追求。双方默契,并且等价。我常常感到它的存在,客观存在的生活就是我创作的生命”。生活的海洋是雷加散文特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只有尊重生活,对生活永不满足,才能得到生活的赏赐。辛勤耕耘一生的雷加获得了艺术的硕果。1980年雷加的作品《江河恋》获“十月文学奖”,1983年《北疆特写》获“解放军文艺”奖。他的《半月随笔二集》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
雷加的散文特写以深厚的生活基础、独特的语言风格、鲜明的思想主题和多层次的审美内涵站在时代的前列,如号角激励人民向着未来、向着真善美进发,又如歌者颂扬人民为实现梦想而忘我奋斗的精神。他们这一代人的文学人生和作品闪耀着历史诗性的光芒,照耀着未来。
虽然雷加的文学人生在当代人们的视线中渐行渐远,读他作品的人似乎已不多,知道他的人也越来越少,但他的文学道路和作品构成的人生,在历史的诗性中尽显一代文学风流。
我对雷加说:“历史会告诉未来,你们是一代有伟大理想的文学艺术家,你们的人生道路和文学作品已与历史时代融为一体,翻阅你们这一代人的作品就是在阅读一段史诗,也是在解读你们的人生和时代,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这一代人的价值和意义。”
他仰头笑说:“未必。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时光岁月最易把人抛。” 他的文思敏捷,充满诗意之思。
献给时代的精神鲜花
与雷加最后一次见面后不久,雷加忽然给我来电话说:“住了半个多世纪的右内大街42号院的老房子要拆迁了,我已搬到通州女儿甘栗家住,欢迎你到通州家里来。给你寄了一本我新编的书《生活的花环》,注意查收。”我与他约定去通州看他。
雷加晚年在他女儿甘栗的协助下,先后整理、编辑出版了《雷加文集》《雷加作品自选集》《雷加日记书信选》《生活与美》《延安世纪行》《我属于这条大河》。这些书每出一本,他都会及时写上我的名字寄给我。《生活的花环:雷加文学回顾》是他女儿编选的一本作品集,这一本本作品集是他留给我的珍贵礼物,也是他留给文学艺术界的一份不可多得的文学史料,是他献给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后一束思想和精神的鲜花。回望雷加艺术人生的每一阶段,细数他的作品和流年岁月,捧着他的书,我的泪水模糊了双眼。
2009年3月10日,雷加女儿甘栗传来噩耗,说她父亲走了。我多么无知,忽略了94岁高龄老人的脆弱,阴阳两界的无情。我悲泣不止,遗憾万分。数月之隔,却是与他永远的告别。
雷加的告别仪式简朴、肃穆,没有场面上的人物,没有盖棺定论的悼辞。他静静地躺着,平静安详,党旗覆盖着他,鲜花簇拥着他,他要启程远行了。只有儿女子孙、亲朋好友的深情怀念和哀思。他一生不尚喧哗,他一生只有奉献,与他一生经历的轰轰烈烈的时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把花环轻轻地放在了雷加的脚下。这花环是崇敬,是祭奠,是悲戚的泪水,是永远的追思。
他将乘那烈焰火龙直上九霄,永不归来。是谁在提醒,不要忘了,一定要让他带上那支一生携带的生花妙笔。那支笔插在了他的上衣口袋里。雷加会用那支笔在浩瀚的星空划破寂寞,绘出五彩云霞,让我们时时仰望他;他也会用那支笔将那云雾化作七彩雨,永远润泽大地和亲情。大爱无界,大爱永恒,我们将与他永远在一起。
2015年1月28日,中国作家协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雷加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当我听到中国作协领导对雷加的文学人生和作品做出的总结和高度评价,以及与会的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雷加文学人生的深情追忆和评述,我感到,这是党和国家及人民对雷加和他们那一代人的文学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肯定,是对一个文学时代和雷加文学人生的深深敬意。正是他们的肯定和敬意,解答了雷加长期的追问。让历史告诉未来,这是历史的馈赠,是生活和时代献给雷加的花环。
(作者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原副院长、教授,广西北海艺术设计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