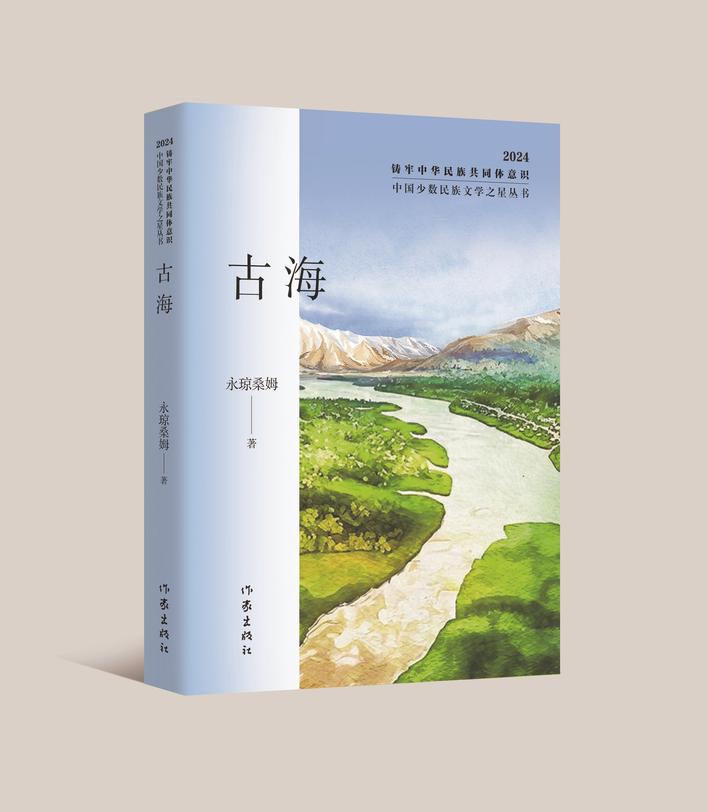牧歌悠悠。
古象雄文明源于她,以阶梯式向雅砻河谷蔓延,侵袭进茂密的塔工地界,再不断向外延伸,成为远古极具影响力的文明,高原之人被其护佑。之后,吐蕃的盛起与衰落都在雅砻河谷里,其后人最终却选择到阿里去栖息,从此停止了征伐,刮起了弘法的劲风。这高地上有了神山冈仁波齐,有了神湖玛旁雍错,有了古格王朝,有了札达土林,使她的声名被高原雪域的风吹向各个角落,成为令人神往的一处高地。
诗人永琼桑姆就出生在这片高地上,她被孔雀河所喂养,目光所及之处被巍峨的土林所占据,使她在柔弱如水与坚毅豁达间穿行,并热爱上了诗歌,想用一行行简洁的文字,表达对故土的那份痴爱和思念。她与西藏当下的许多年轻人一样,最初在家乡的学校读书,后来考取到内地的中学上学,然后考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毕业后再回到家乡发光发热。这种经历使她与故乡之间保持了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情感上的丝丝缕缕甚至因距离而让她对故乡有了一种审视与考问,这在她的诗篇《铁匠的女儿》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是你吗?铁匠的女儿/与我一起放学回家吗?//越过了五彩塔/乌塔粮仓与马车在灯边/有我们共同回家的大路//呼啸着的塔下魔/用狂风的劲绳 捆住了街道与细沙/让我们紧紧拥靠在一起……”
虽然已经进入了21世纪,但偏远的故乡却仍被旧有的观念所束缚,人们对手工艺人的轻蔑与不屑依旧存在,这让年轻的诗人既疑惑又愤慨,于是情不自禁地对这种顽固的思想进行回击,而且讴歌劳动的光荣与劳动者的美,表达了人人平等的思想:
“雪中一阵玩闹的风/使老人的曲调颤颤巍巍/但也继续哼唱他的历史/缅怀他的青春/匆忙的雪粒也在附和着落地/贴紧他曾守卫的土地//氆氇上老人还有一部留声机/白内障折磨地夺取了一切洞察/幸好他的声音仍在传颂着英勇的旋律……”
《遗忘的人》描述了一位说唱艺人,可是这位艺人已经风光不再,只剩下衰老与病痛,但他传扬英雄的使命不会因岁月的侵蚀而终止。他坚持用苍凉的声调继续吟诵英雄的故事,为人们提供精神上的滋养。这样的画面,令我们动容,也使我们不免为岁月的匆忙消逝发出一声喟叹。还有《外婆》《益西》《柏树香》《普兰的春》等许多的诗篇,都是因写故土而情感喷薄欲出的。
永琼桑姆这部集子里的诗歌篇幅都很短,有些甚至只有那么几行,但这并不说明其诗歌的空泛或简单,反倒证明了她的极简与匠心独运,比如《母亲》只有“一团柔软的蒲公英/任风吹散 细碎的情绪/只剩一根 干枯的 母亲”这寥寥几行诗,却让我们读到了母亲从青春到年老这几十年的变化。在柔软的蒲公英这个意象中,诗人淡化了许多的愁绪和伤感,让读者在美丽的诗行中接受这种残忍的现实,其力量是无法言说的。
“你是桌子里/深藏的尼泊尔木碗/一壶茶/滚滚浓烈而来/你总是宽容那片热情/却不留下脉脉的余温”。《余温》这首诗的意指可能有多种,如爱情、亲情、友情等,这种丰富性使得它拥有了更多解读的可能。
“野杜鹃是山神自残的血痕/光照充斥在满足的紫色上/人们编织着花冠佩戴着美丽/山神编织血肠祭祀着杜鹃”。《杜鹃》这首诗写出了大自然里的因果关系,到底是谁在成就着谁?这是一个带有哲思意味的疑惑。
永琼桑姆诗歌创作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形式上的努力探索,有时一个字开头,有时三个字,有时十几个字等,但通览下来你就会看到各种形式的排列,这些都是诗人故意为之,也可见到她的不拘一格的创新意识。
年轻的永琼桑姆刚刚踏上诗歌创作的道路不久,前方的路还很漫长,需要提高的地方还有很多,唯其稚嫩,更具希望。期待她通过不懈的努力,争取成为一名更加优秀的诗人。
(作者系西藏作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