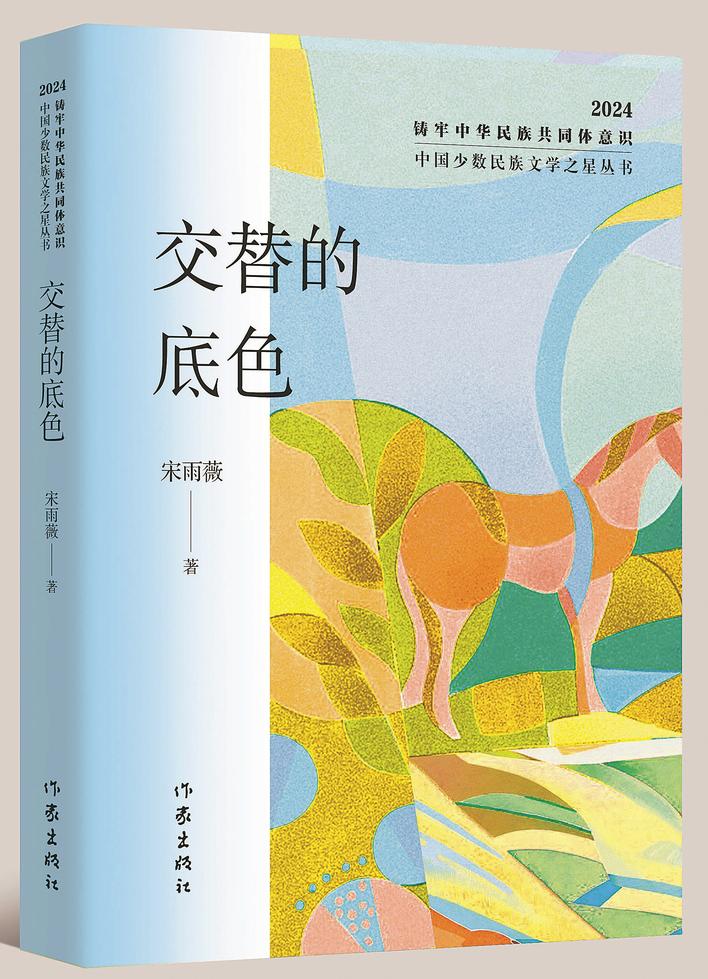品鉴雨薇的散文,别有一番滋味。有小惊喜,也有小得意,却不显得傲慢。大道至简,无非化虚为实,无非化实为虚,虚虚实实构成其作品的风姿与气韵。常言道,女人是水。水满则溢,在她的思想、情怀、趣味与语言之中,浮现出散文的灵魂。
日常的雨薇,总是一副机关文员的模样,坚韧、坚强、坚定,感染着身边的亲朋好友。她对自己的要求近乎苛刻。2018年9月,敦化笔会聚集了吉林散文界的各路豪杰。结束那天上午的恳谈会,由我主持。我随我的意,请雨薇最后一位发言。之前,她一直埋头聆听,叫她时,她有些不知所措,但终究从容应对,自顾自倾诉,不知不觉讲了竟然半小时以上。与会者沉浸在她讲述的乡亲、乡事、乡情与乡悟,没人起身走动出去抽烟、上洗手间,完完全全沉入了她的讲述之中。后来,她的作品出现在《人民文学》《民族文学》《安徽文学》《四川文学》等文学刊物上,还作为现代文阅读考试题出现在河北、浙江、黑龙江、甘肃及北京等省市高三语文试卷上。这,就不是“水满则溢”了,而是“汩汩流荡”啊!
雨薇的根系深植于村庄,纵横交错,无法断绝。那个遥远的村庄,在长白山的褶皱里艰难生长,稀稀落落的五六十户人家,人人精耕细作,种植玉米、大豆、白菜和萝卜,物产并不丰富,但他们一直勤勤恳恳地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样的乡村记忆一直在雨薇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尽管她自中学阶段起就离开了此地,但她与这个村庄始终在岁月中缠绕,最终在岁月中回归。故土的光芒明明灭灭,闪亮了昨天,闪耀着今天及明天。那个地处穷乡僻壤的小小村庄,她很少提及它的名字,因为那个名字总是在出现时使她莫名地心疼,仿佛想起它,就想起那里艰辛的生活。可是每当她想起那个生活过的小村庄,思绪飘飞时,她总是忍不住落笔,那些发自内心的文字最终就成为眷恋故土的优秀散文了!
哦哦,她的散文,那么透彻——
“坡高路滑,我弓着腰,背着麻袋,向坡上一次次攀爬的身影,渐渐地拉大着山坡的弧度。在那片让父母充满希望的田野上,每一次,我都要上气不接下气地,将一袋袋的玉米棒子,挣命地从坡底背到坡上的路旁……”
哦哦,她的散文,那么清脆——
“很多时候,我喜欢看着四叔对准白桦树段,在那个树的年轮中间圆圈的部位,高高举起斧头,手起斧落,一声清脆的声响,白桦树段一分为二炸裂在四叔的脚下,就像是碎了一地的梦想……”
细节,细节……细节怂恿着雨薇,一枝一叶总关情。看到一句话:“时间让深的东西入骨,让浅的东西无痕。”入骨也好,无痕也罢,毕竟要写出散文的气息、气运与气度。所谓散文之散,所谓散文之文,关键就在那一闪而过的灵光哩,要问灵光最终去哪儿——牧童遥指杏花村!
新文学以来,现代白话散文的成就一波接一浪,一浪接一波,波追兮,浪飞兮。萧红、张爱玲等女作家,贡献出许多不俗甚或不朽的散文名篇。雨薇不肯仅仅站在她们身后,而是尽量踩着光影追上去。
雨薇在村庄里度过了少小年月,看惯了也看懂了那些庄稼树木,它们之所以长势喜人,必然是经得起风,淋得起雨,熬得过霜雪雷电,挺得过酷暑严寒。更何况,山、水、人,久养而性成,习得了那种倔强的品性。体现在作品上——你写你的,我写我的;体现在做人上——你行你路,我行我素。
就散文来讲,没有技巧,就是最好的技巧。境由心生,文由境生,若人品干净,文品自然圣洁。呼吸在市井,低眉顺眼,块垒无计消除;而到了草原上,策马扬鞭,境界一下子就辽阔起来。当然,叙事讲究调性,一笑了之抑或一哭了之,小儿科,免不了轻慢艺术。雨薇凭她生活的底蕴和思想的高格频频出手,字词句段中融入了大爱与深情,无为而无不为!
雨薇心中深藏不知多少事,散出来的千字文、万字文,情幽意远,夺目亦夺魂。
许是去年秋天吧,我受邀参加某个活动。其间,碰到了雨薇,得机会与她交谈,核心话题是生态散文。我曾经写过若干篇什,没怎么把这当回事。年轻些的雨薇呢,却特别担心丰富的生态题材会掩盖自己思想的短板。于是,她积极地收放眼力和心气,开垦着一片又一片小散文、大文章。握别的时刻,我突然发现她姣好的脸庞隐约透露出沧桑。不由得暗想,沧桑兴许是雨薇散文又进一步的体现吧?
一个人,活成了俯仰于天地之间的作家。谨以此文致意,为雨薇,为散文,为雨薇的散文,也为自己的散文。
(作者系吉林省作协副主席、吉林省散文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