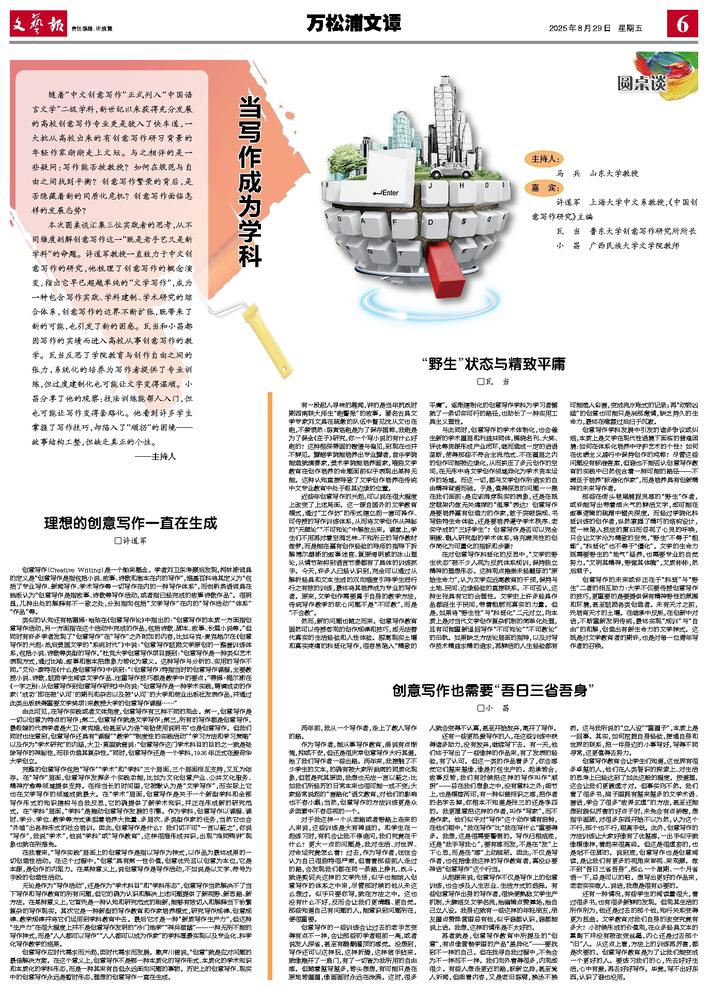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趣闻,讲的是当年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师生“跑警报”的故事。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刘文典在疏散的队伍中瞥见沈从文也在跑,不禁愤然:陈寅恪跑是为了保存国粹,我跑是为了保全《庄子》研究,你一个写小说的有什么好跑的?这种根深蒂固的傲慢与偏见,到现在也并不鲜见。舞蹈学院能培养出专业舞者,音乐学院能造就演奏家,美术学院能培养画家,唯独文学教育在创作培养的命题面前似乎表现出某种无能。这种认知直接导致了文学创作培养在传统中文专业教育中处于极其边缘的位置。
近些年创意写作的兴起,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上述局面。这一源自国外的文学教育模式,通过“工作坊”的形式建立起一套可操作、可传授的写作训练体系,从而将文学创作从神秘的“天赋论”“不可知论”中解放出来。课堂上,学生们不用再对着空洞乏味、不知所云的写作教材做梦,而是能在富有创作经验的导师的指导下拆解博尔赫斯的叙事迷宫、复原海明威的冰山理论,从情节架构到语言节奏都有了具体的训练抓手。今天,许多人已经认识到,完全可以通过从解析经典和文本生成的双向维度引导学生进行行之有效的训练,最终将其培养成为专业的写作者。原来,文学创作需要属于自身的教学方法,传统写作教学的核心问题不是“不可教”,而是“不会教”。
然而,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创意写作教育固然可以传授客观的创作规律和技巧,却无法替代真实的生活经验和人性体验。脱离现实土壤和真实疼痛的科班化写作,很容易陷入“精致的平庸”。逐渐建制化的创意写作学科为学习者铺就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也助长了一种实用工具主义理性。
与此同时,创意写作的学术体制化,也会催生新的学术圈层和利益共同体,围绕名刊、大奖、评优等资源形成产业闭环,继而造成一定的话语垄断,使得那些不符合主流范式、不在圈层之内的创作可能被边缘化,从而挤压了多元创作的空间,在无形中将文学创作领域异化为学术资本运作的场域。而这一切,都与文学创作所追求的自由精神背道而驰。于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一一摆在我们面前:是应该洞穿现实的表象,还是在既定框架内做无关痛痒的“温厚”表达?创意写作是要培养富有创造力的作家,敢于突破陈规、书写独特生命体验,还是要培养遵守学术秩序、老实守成的“三好学生”?创意写作是否可以完全照搬、融入研究型的学术体系,将充满灵性的创作简化为可量化的指标和步骤?
在对创意写作科班化的反思中,“文学的野生状态”被不少人视为反抗体系规训,保持独立精神的理想形态。这种观点推崇未经雕琢的“原始生命力”,认为文学应远离教育的干预,保持与土地、民间、边缘经验的直接联系。不可否认,这种主张具有它的合理性。文学史上许多经典作品都诞生于民间,带着粗粝而真实的力量。但是,如果将“野生性”与“科班化”二元对立,则本质上是对当代文学创作复杂机制的简单化处理,且有可能重新退回写作“不可知论”“不可教论”的旧轨。如果缺乏方法论层面的指导,以及对写作技术精益求精的追求,再鲜活的人生经验都有可能落入俗套,变成流水账式的记录;再“动物凶猛”的创意也可能只是刹那激情,缺乏持久的生命力,最终在喧嚣过后归于沉寂。
创意写作学科发展中引发的诸多争议或纠结,本质上是文学在现代性语境下面临的普遍困境:如何在体系化培养中守护艺术的个性?如何在优绩主义盛行中保持创作的纯粹?尽管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谁也不能否认创意写作教育的实践中已然包含着一种可能的路径——不满足于培养“标准化作家”,而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未来写作者。
那些在街头巷尾捕捉灵感的“野生”作者,或许能写出带着烟火气的鲜活文字,却可能在叙事逻辑的疏漏中错失深度。而经过学院化科班训练的创作者,纵然掌握了精巧的结构设计,若一味陷入技法的窠臼而忽视了心灵的呼唤,只会让文字沦为精致的空壳。“野生”不等于“粗鄙”,“科班化”也不等于“僵化”。文学的生命力既需要野生的“地气”涵养,也需要专业的自觉努力。“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创意写作的未来或许正在于“科班”与“野生”二者的相互助力:大学不仅要传授创意写作的技巧,更重要的是要提供保有精神野性的氛围和环境,甚至鼓励各类创造者。未有天才之前,先培育天才的土壤。在继承中反叛,在创新中对话,不断重新发明传统,最终实现“规训”与“自由”的和解,创造出有新生命力的文学样式。这既是对文学教育者的期许,也是对每一位青年写作者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