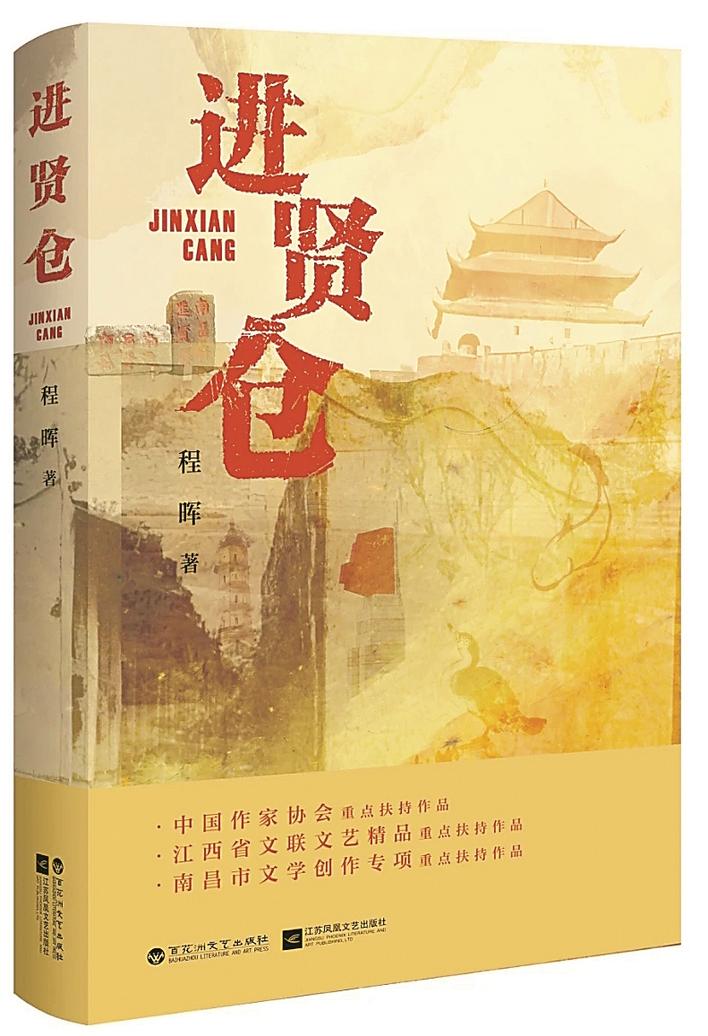我在江西南昌老城区丁公路那座建于20世纪90年代的小区,住了15年。书房的窗口,正好对着一棵枝丫虬结的老樟树,老樟树的下面,是一段老南昌的青石板路。每天晚上坐在书房,便和这棵老树互相看着,日复一日地沉淀着过去与未来。开始写《进贤仓》以后,我们的交流似乎更加频繁,那些藏在树影里的岁月、青石板下的往事,都顺着目光流淌而来,直到《进贤仓》最后一个字落稿。
我生平第一次到南昌,是因为1993年夏天的一场诗歌大赛。那天,主办方安排我们去参观八大山人纪念馆。当我的脚步刚刚迈入青云谱那座青砖灰瓦的院落,目光触及朱耷笔下的禽鸟、孤寂的山石时,心中忽然泛起一阵强烈的震颤。这是我与南昌文人精神的第一次正面碰撞:那些看似怪诞的笔触里,如此深刻地藏着一个文人的孤愤与苍凉。从此,南昌对我来说,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符号,而是一座浸润着文人血脉的城市,那些隐匿在弄头街巷里的故事,连同八大山人画卷里的那些墨痕,在我的心底最深处悄然晕染开来。
后来到南昌工作,天天走在岔道口西路的那段青石板上,听人们讲伶伦造律、许逊治水的故事,才慢慢懂得,南昌城低调的内心藏着太多的故事,骨子里更有一股令人敬佩的“隐士气”。从汉代悬榻拒仕的徐稚,到宋代躬耕隐居的苏云卿,再到清初遁入空门的朱耷,这片土地始终是特立独行灵魂的栖居之所。他们如深谷中的幽兰,不慕尘世间的繁华,却在历史的暗角里坚守着独有的精神根系。
在创作《进贤仓》之前,我几乎所有的小说都盘桓在故乡那片土地和与之相关的生活经验里,直到我的“乡绅三部曲”完成以后,心中有一个念头不可抑制地迸发,我要写南昌,不是作为背景去写,而是要进入南昌的纵深,抵达精神内核。
我家楼下岔道口西路的路口,有一对老夫妻开了家小店,他们家独创的纸包鹌鹑和鲜炒田螺,每天吸引着成百的食客,但他的店门口有一块颇显任性的木牌:酷热歇业,严寒休市。每年到了那个时候,夫妻俩门一关,天南海北旅游去了。旁人都笑他们迂腐,有一次我甚至问了男主人,他的话让我感慨良久:糊口而已,何必拼命?这种看似不合时宜的执拗,恰是南昌文人精神的现代性投射。他们未必能背诵八大山人的诗文,却本能地继承了那种“超脱不阿”的生活姿态,这股不攀附、不将就的劲儿,像老樟树的根,深深扎在南昌的土里,也让我看清了《进贤仓》要追寻的风骨,那些过去的东西,有些会在当下延续,并终将通向遥远的未来。
《进贤仓》就从这根里面艰难地生长出来。我一向认为,小说重要的不是真实性,而是要让读者感受到真实。进贤仓是一个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街区,我在这条“街”里抠出了小说里的故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进贤仓街是否真的存在,并不那么重要。牛氏家族五代人,改朱姓为牛姓,却不改骨子里的文人基因。我写他们在时代洪流里的挣扎,不是想记录历史,也不是想为他们立传,是想写那些乱世里迷茫和坚守的人们,在过去命运与个体选择的碰撞中,产生能触动读者强烈共鸣的东西。
汪曾祺先生曾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对此,我深以为然。我长期在机关从事文稿撰写工作,程式化的语言惯性让我此前的作品屡被诟病缺乏文学质感。为了摆脱“公文腔”的束缚,我重新拿起那些中外经典名著,研读他们的语言特色。经常到南昌的老茶馆,听老人们讲“仓前仓后十八巷”的掌故。夏天的夜里,我会到人员密集的老福山立交桥下面,收集那些带着江风与稻穗气息的俚语,记录老人们充满地域特色的对话。我甚至还会模仿牛淼有的语调与朋友交流,让对话里流淌着老南昌的原汁。
《进贤仓》写完了,我常常看着窗外的那棵老樟树发呆。老南昌的话、进贤仓街的风还有那些藏在历史里的魂,借着我的笔流出,如同一列满载岁月传奇的火车,从时间的纵深处向我们驶来。在这个短视频、直播深受欢迎的时代,讲述一段这样厚重的百年故事,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我仍然固执地认为,越是碎片化阅读时代,能够读这种有历史感故事的人,都是这列火车中有缘的乘客。我只是一个故事的转述者,把老樟树的私语、青石板的记忆变成了文字。至于好不好,我不知道。只知道书房外的那棵老樟树又抽了新芽,根须深深地扎在泥土里,攥着那些欲说还休的年月。而我,想着把这些年月舒缓地摊开,让更多的人看见其中深藏着的微光。那应该是过去与未来在当下交汇的回响,也是生活与文学碰撞后,产生的永不熄灭的光芒。
(作者系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