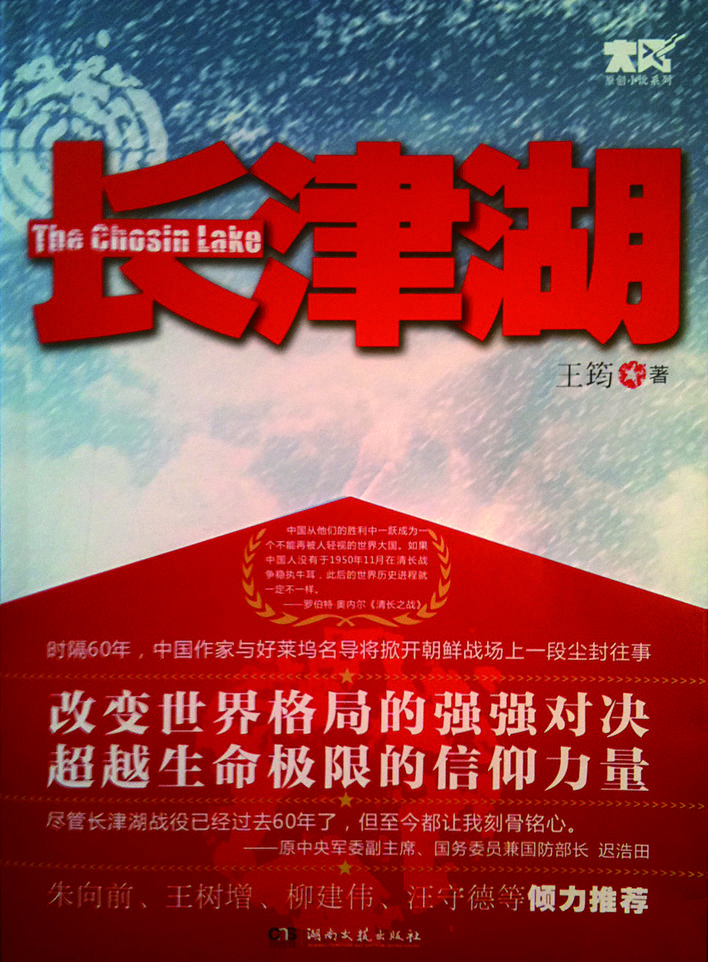就当下战争题材作品而言,不再仅是对阶级斗争、民族冲突的简单描写,必须要包括对人性的弘扬、信仰的彰显,才能使作家笔下的战争更加有历史感与时代感。因为在和平年代出生并成长的我们这代人,只能通过这些文学作品才能完成对20世纪那一系列战争的洞察,但这种洞察乃是基于对人性闪光点的捕捉,而不是激起仇恨、崇尚暴力,从这点来说,王筠的长篇小说《长津湖》是一个很好的文本范式。
在卫星地图上看长津湖,是朝鲜一块极不规整、处于崇山峻岭之中的庞大水域,此处虽险峻苦寒,风景亦应壮美辽阔,但《长津湖》却以美式大片的笔触反映了作为战场的长津湖之残酷。世界战争史公认,长津湖战役是美国军队在战史上最远的一次败退,更是抗美援朝战场上最为惨烈的战役之一,但历史告诉我们,越是残酷的战争越能激发人性中最本质的一面,王筠笔下的长津湖战役也不例外。
作为当代文学中一个长盛不衰的战争主题,抗美援朝这一题材在不同的作品中一直发生着时代的嬗变。尽管这些作品都不约而同地告诉我们:这场战争永远是中美双方军力的较量,但《长津湖》所着力笔墨之处,是力图还原并回归人性的历史现场——在极度残酷的恶劣条件下,作为军人的中国志愿军甚至美军士兵是如何克服困难、获得涅槃似的新生。
因此,《长津湖》的核心意义在于,它以文学文本为载体,试图以文化的冲突为视角来诠释和平的价值与人性的升华。它坦诚地告诉所有的读者:长津湖战役之于中美两国军人来说,都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劫难,气候苦寒、语言不通、思乡之情与物资短缺等致命问题均使中美两国军人同时“遭罪”。没有拘泥于“扬我贬敌”的二元斗争思维的叙述,体现出了作者厚重的人文情怀。无疑,这是当代文学史中关于抗美援朝叙事的重要超越。
小说以对文化冲突的阐释,叙述了战争让两国军人完成了对彼此“从好奇到了解”的全过程,但这个过程的代价却惨重无比。我们可以看到,吴铁锤的锣在《长津湖》中是一个重要的符号,它曾使美国人闻风丧胆,也曾让志愿军暴露信号。但归根结底而言,这个元素是中国化的,之于美国人来说,神秘的锣声意味着中国军队的迫近,可他们对于这个乐器又是如此地陌生,以至于听到锣声响便“就地隐蔽”。同样,刚刚入朝的中国军队对于美国人亦基本上一无所知,无论是吴铁锤还是孙友壮,他们面对“美国香油”、睡袋与美式武装时,表现出来的好奇、惊诧,堪称妙笔之行文。但经历了这场战争之后,无论是志愿军还是美军,他们均不再用惊异的眼光来审视“敌人”的一切。我们还必须看到,《长津湖》里对于志愿军战士“来源”的设置,亦反映了作者的良苦用心。可以这样说,这一设置是刻意的,它彻底颠覆了先前类似题材小说里简单的“贫苦大众”格局。《长津湖》里的志愿军战士来自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其中既有受地主迫害的失地农民,也有国民党部队的投诚士兵,甚至还有投身革命的上海滩知名导演、教会学校里的女学生与英国洋行里的职员。作者之所以如此设置,恐怕很大程度在于表明这支志愿军不再是一支简单的军队,而是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甚至四亿中国人乃至深厚的中国社会和文化了。
《长津湖》里作为符号的一个角色不得不重视,那就是志愿军前卫营教导员欧阳云逸,在这场战役中实际上担任了一个文化冲突调解者的角色。因为他见多识广,操着流利的英语,所以无论是对战俘喊话,还是与俘虏交谈,甚至翻译缴获的情报,他每时每刻都起着“支点”的作用,他的出场甚至还使得美军军官改变了对中国军队的看法。尤其是与战俘麦卡锡的一席对谈,堪称小说中最为出彩的一段。在对谈中,麦卡锡认为“当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念受到挑战的时候,我们有责任来维护它”,而欧阳云逸则以“中国的文明博大精深,你理解不了也是正常的”回应之,姑且不论这样的对谈是否真的在战争中出现过,但至少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了作者以文化冲突为叙述视角的良苦用心。描摹文化冲突,彰显人性美好,这应是作者的初衷。中国军人优待美军战俘,美军战俘多次向中国军人致谢,受感化的美军军官向俘虏们喊话,以及中国军人在高寒阵地上的相互支撑、彼此关怀,在《长津湖》里已不再是先前的“阶级感情”,而是对阶级、国界与种族的人道主义超越。须知以人性为核心、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在任何战争中都是最可贵、最值得借鉴与反思的。
借此,笔者认为《长津湖》是当下军旅小说中抗美援朝叙事的丰富,因为它首次突破了两个阵营的政治对立,从文化冲突的角度弘扬人性的光泽。除此之外,《长津湖》还强调了“信仰”的意义并对这一概念进行了人性的诠释。中国军队凭借顽强的意志战胜了美军,他们所拥有的是顽强的信仰,这是发人深省的。
“信仰”是一个与“人性”共生的文学母题,信仰会使得坚持更有意义,这便是志愿军战士们不怕牺牲、屡挫屡战的精神动力,但小说中却没有将这个信仰简单化,这里的信仰不再是先前类似题材小说中的“红旗插遍全世界”这一伟大革命理想,而是中国人普遍的家国情怀,因为是异乡作战,这一情怀自然就变成了对于家乡、祖国的信仰性思念——譬如对于台湾籍志愿军人员、导演出身的凌子林而言,他的信仰只是打完仗“回到上海,再回到台湾”;来自苏北农村的前卫营营长吴铁锤的信仰则是“打完了龟儿子陆战1师,就娶媳妇”;而洋行职员出身的欧阳云逸与师医院护士蓝晓萍的信仰则是彼此的爱情约定。在这样的信仰下,他们勇敢地坚持着战争必胜的信念,最终挫败了装备齐全的美军陆战1师。归根结底,这样的信仰依然基于人性的光泽,并由特定的中国文化结构所决定。战争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信仰所促成,但这个过程与结构又非常复杂。《长津湖》为我们提出了许多之前未曾深入反思过的问题——人性的彰显在战争中究竟能否战胜简单的胜负结果?究竟什么样的信仰才是战争中最核心、最关键的因素?因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实际上更能反思出人性在战争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毕竟,和平的追求最终将归结于人性的美好,战争的胜负无疑更彰显出信仰的珍贵,但在历史的长河中与人道主义的基石上,胜负已然不再是一场战争惟一和关键的评量标准了。
历史地看问题才能对战争有更全面的反思,《长津湖》十余次用了“多年之后”这一“马尔克斯句式”。小说中幸存者们的表述,使得整个战争的场景更加真实生动,老战士们安详的晚年生活,愈发渗透出信仰的强大、人性的回归与和平的可贵。
这个世界上的任何战争都是残酷的,但承载战争的历史却是真实的。透过《长津湖》这部小说,我们不但可以深深地感触到历史的厚重、苍凉与真实,更能从战争的角度来聆听人性与信仰共奏的雄壮交响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