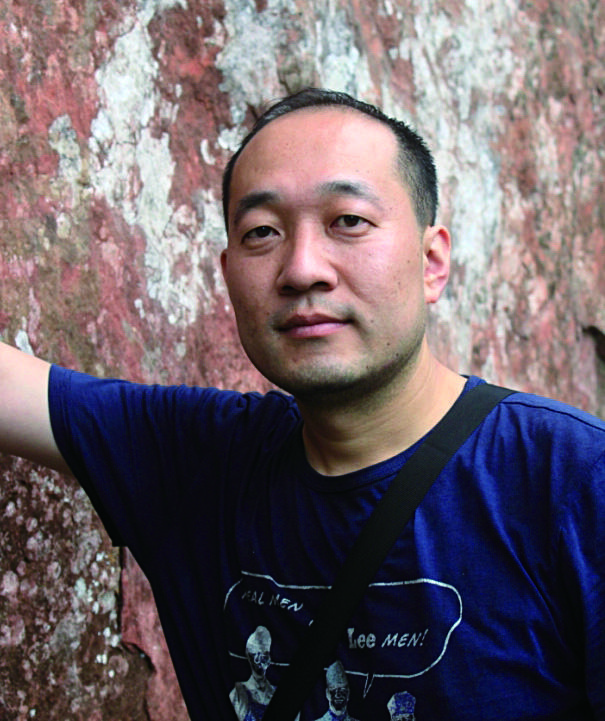这几天在内蒙出差,从满洲里一路南下,途经呼伦贝尔、兴安盟和锡林郭勒,满眼尽是没有边际的绿色,看得我眼睛差不多都绿了。如此海量的绿我平生所未见,但我却总有种似曾相识之感。一天早上,我们坐车离开东乌珠穆沁旗,从车窗望去,我突然发现这草原地貌与我熟悉的阿拉善右旗的茫茫戈壁竟然如此相似,那空旷辽阔悠远苍茫的感觉如出一辙,包括平缓起伏的大地、远方微曲的地平线和直白热烈的阳光,甚至也包括那些云朵的形状。区别只在于它们的色彩,一种碧绿,一种苍黄。
每次一想到戈壁,我就很想写小说。我同朋友聊天时,十有八九会把话题扯到我待过的巴丹吉林沙漠和河西走廊。我的小说也十有八九会让人和事在那片戈壁大漠中发生,因为我觉得如果把他们扔到城市里,就像把鱼扔到沙漠里一样,一切都将无法成立。可说来惭愧,在戈壁滩服役的那些年,我也经常会厌恶那里的贫瘠、风沙、单调和某种不确定的绝望,会悄悄地想着能快点离开这个我在小说里反复描述过的荒凉之地。我完全不确定我是否爱它或者爱过它。即使现在让我重新选择在何处生活,我一定也会选择哪怕是住房更挤、空气更差、从来都看不到地平线和星河的城市,虽然我心里从来也没有真正喜欢过都市。所以我会觉得这一切有点荒唐:我最想离开并且的确已经离开的地方,却是我最怀念又最能诱惑我书写的地方。同理,我也时常觉得自己很虚伪,自己心知肚明的那种虚伪。
这种矛盾同样存在于我的那些笨头笨脑的小说里。特别是在我最初写小说的那几年,我总喜欢充满感情地描述戈壁和其中的军营生活,可实际上我当初的感觉复杂多变,无法简单地被文字处理。因此在小说中,我更多的时候故意隐瞒了我最真实或者最阴暗的想法,理由是我认为那种正常但庸俗的想法背离了军队——不仅是中国军队——所崇尚的精神和道德。从情感上讲,我真的无法也不愿违背这种精神和道德,因为这是军事集团和军人职业所不可或缺的要素,即便地球人都知道战争是最为残酷的人类行为,可这种精神和道德仍然会被赋予某种预设的或是先验的崇高感。这与军队的使命密切相关。何况从17岁进入军校开始,我至今已有了结结实实的20年军龄,军队职业精神的许多成分,我自己也一样认同。但认同与实践是不同的。这无疑是一种人为的拔高,哪怕我已经竭力让它不那么显眼。每到这种时候,我会安慰自己:我做不到的,并不见得别人就做不到。军队就是军队,军队自有军队的一套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既然这样,让我写一下我想象中远比我更优秀、更有情怀的军人又有何妨?
很久以来,我差不多一直都在这样安慰自己。我身为军人,也了解军人,特别是艰苦环境下的基层军人。由于集体生活的共通性和军事生活的特殊性,他们往往被严格的纪律约束,不可能肆意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观点。从这个角度来看,用被规制的写作来表现被规制的生活,其实也没什么不公平。事实上我相信,生活永远不可能像草原或戈壁的空气那样澄明。地平线很远,能见度有限,视野的局限和文字的局限永远存在,所以一切写作都会受到原因不同的规制,一切作者都会进行标准不同的自我审查。也许问题的关键正在于这种规制的程度。对我而言,我一直试图寻找这种规制的边界,有时是军人的视角,有时是作者的视角,有时是军人作者的视角。这种寻找让我越来越感到,自己在离需要勒马的悬崖还很远的地方就已经开始用脚尖探路,进入临深履薄的状态,仿佛一个进入雷区的士兵,每走一步都战战兢兢,其实脚下离我所担心的雷区还异常遥远。这样造成的局面就是,当我故意隐瞒了一部分真实的时候,剩下的那部分看上去便成了假象,虽然它本身也是真实的。我过早过快地规制了自己的想法,好比一匹还没来得及撒开四蹄就被我勒住了笼头的郁闷的马。
后来我想,我应该彻底卸掉这匹马的马具,把它重新放归草原,不论锡林郭勒还是呼伦贝尔,哪怕阿拉善也无所谓。它想怎么跑就怎么跑,它想跑多远就跑多远,没准儿真就会找到更为丰美的一片草原。不过真正的问题在于,草原永远都在这里,真正需要改变的只是自己。至于改变自己,你我都清楚,这可真不是件轻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