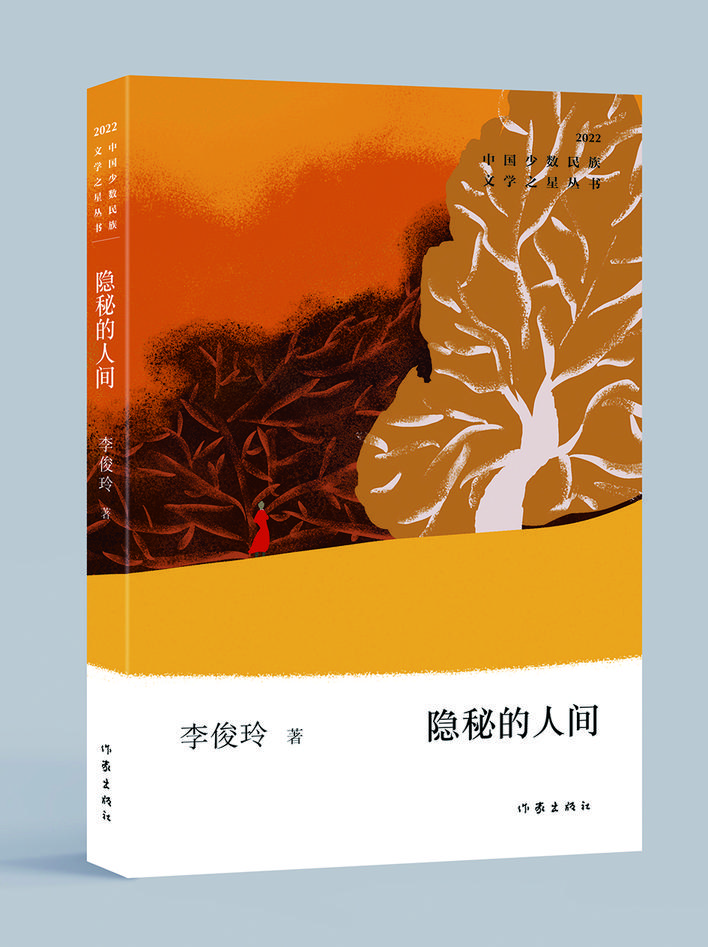我曾在散文《素时光》中,以这样一句话作为题记:“无人问津的巷口,总是开满了鲜花。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那些你曾经觉得虚妄、无助、困苦和孤独的时光,或许在后来会是给予你人生养分的过往。”
我的写作养分最初来自于童年,来自那些和山野耳鬓厮磨的时光。那个仿佛被遗弃在深山的布朗族寨子,需要穿越莽莽丛林才可以抵达。我的父亲是第一个走出大山的人,退休时他是正科级干部,对于生活在深山里的布朗族而言,这是零的突破。父亲敦促我读书,也培养我自立,每到假期就把我送回老家,他觉得那是我们的根脉之地,让我回去,不是体验他曾经的生活,而是让我与那片土地建立感情。吃苦是难免的,多数时间没有电,火把是我们夜晚出行的必备。地无三尺平的地方,必须历练人的脚力,吃食也简单粗糙。我和亲人们一起种苞谷、放牛羊、砍柴、找野菜,在贫瘠的土地上撒播汗水,有苦涩,也不乏野趣。
放牧时,在寂寥的山野听那些穿越云端的山歌调子,思绪便会随之飞翔。夜晚围着火塘,听阿公讲那些白发苍苍的故事,仿佛进入另一个世界。寨子有客事时,和族人们打歌狂欢,一股股尘烟扬起人们对于生活的挚爱,天与地都在我们无止境的踏跳中迷醉。晨起第一碗水是给神灵的,吃饭时阿奶总会端着饭菜敬献祖先。阿奶说,出门靠路人,进门靠亡人,亡人就是我们的祖先,是游走在我们的周遭的神灵,因有他们的庇佑,人们才得以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生存并开枝散叶。这片土地滋养了万物,也滋养着感恩的人群,我们感恩身边的一棵树、一片叶子、一块石头,感恩火与水、土地和流云、山河日月,它们人物化地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让单调的生活变得有趣生动。火塘笑,客人到,连火都以它特有的方式与人的世界达成奇妙勾连,这真的像是一个童话。我庆幸自己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让我对人间保持着最初的敬畏和善意。
我从来没有想到,那些带着魔幻的时光,在后来成为了我写作的资源。我常常在回忆中构建起自己对世界的认知,这些我生命里的成长印痕,随着年岁增长逐渐发酵,让我迫不及待地提起笔来。于是我写下一系列关于那片地域的文章,《祭忆贴》《人间炊米》《宝藏丛林》《火语者》《食事记》等的书写,便是我与自己的心灵、故乡和流逝的点滴再次交汇碰撞的过程。这些文字是我在与世界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后,所找到的留存于自己身体里的精神烙印,是对熟悉生活的洞见和思考。文学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走进早已消失的过往中,重新打捞那些当时自己没能仔细感悟的东西。我在写这些文字时,感受到了沉迷和超拔、痛苦和释然,更多的还是感恩。这种书写很奇妙,让人有种重获新生的快感。
对于我生活了半生的家园施甸,我有太多需要抒发的情感。这座位于怒江边上的小城,历史上是“南方丝绸之路”的必经通道,“姚关人”8000多年前就在此繁衍生息。明朝邓子龙抗缅平叛驻守7年之久,留下五关要塞和驻地清平洞,也留下滋养一方的史诗文脉。滇西抗战,这里是大后方也是前沿阵地,施甸人浴血奋战,与远征军共同筑起日军无法逾越的防线,无数抗战英烈长眠于此。南亚和中原文化在这里相融共生,24个民族携手谱写了属于边地小城的历史。我身处其间,常为这里流传和发生的一切所打动。每一次书写都是回归和进入,我全身心感受着这片土地上人群的精神与心灵,熟悉又带着些许的陌生感。
《小城人物》所写的,就是40年来带给我别样生命感受的人们。他们带着各自的光芒和魅力,成为这个小城的特殊符号。我想通过文字,让他们成为这座小城的集体雕塑,让后来人认知到这座城的时代风貌和更迭。《面相》《有龙在侧》《夏至》《庙宇 庙语》则是对自然生态和民俗文化的感受思考。在施甸,你走进任何一个陌生的人家,都会受到贵宾般的接待。这里的人们朴素、豁达、热情,就算身处困苦之境,也会仰头眺望星空,构建自己的精神殿堂,我因他们而想到了生在石崖却迎着阳光努力生长的青树。他们步伐笃定、神情坚毅,困顿和挣扎都在朴素的信仰里得以化解和消融。和土地相依,与生活和解,向自然学习,这便是他们的生存之道。他们有着相同的生命意识和价值取向,懂得以怎样的方式和自然相处,懂得感恩,懂得人生有度,懂得自我安抚。那些根植在民间的礼仪节庆,包藏着处世哲学,也寄托着高贵情感。
作为一名女性写作者,我的书写更多是面对着琐碎生活和身边的亲人,也对女性进行剖析。《李劳动的幸福》《见字如面》《心内科的日子》《父亲的习惯》《小恙小记》《距离》等都是对亲人的叙写,我们从亲人身上感受温暖、获取力量,也在不断成长、学会珍惜。生离死别、爱恨情仇,或风轻云淡或跌宕起伏,每个人境遇各不相同,我想书写只属于我的生命体验。在女性话题上,《秋风恸》是我写得比较沉重的一篇散文,它写到了女人的卑微和艰难。我们在经历生产之痛、养育之累的同时,还承受着世俗的轻慢和忌惮,这是父辈们一生挥之不去的隐痛,也是我们这代人难逃的窠臼。我因为属虎且在秋天出生,结婚时不得不喝下夫家灭“虎威”的“八井水”,表姐因为属羊,在婚姻问题上累累遭挫,不得已远走他乡。我们都经历了鄙陋世俗带来的伤害,也因此更懂得对人世悲悯和怜惜。
阿奶曾对我说过,我们今生之所以成为亲人,是前世跨越了千山万水才走到一起,不知走烂了多少双鞋子。她一生劳苦却从不抱怨,快去世前还拖着病体和前来探望的亲友开玩笑。这个没有读过一天书的布朗族老人,其实是最有学问的智者,她的处世方法为我们的前行之路点亮了一盏灯。亲人们是因有了为彼此奔赴而来的那份缘才相聚,我想写作也是这样,和这个世界间的纠缠,注定要我用文字的方式来表达。幸甚我一直从事着这份工作,且热爱着。
《隐秘的人间》写了一些从小到大听到的鬼神之说,在那个娱乐苍白的年代,老姑婆的鬼故事就是孩子们的精神盛宴,害怕而向往也成了我们对这个世界最初的认知。直至今日,我都会对眼前的人间抱有足够的敬畏。之所以用《隐秘的人间》作为散文集的题目,是因为我觉得,在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人间外,还有我们看不见的人间,比如我们的内心世界,比如“举头三尺有神明”,我想以这个标题作为这么多年来对写作的一种敬拜。
从一棵树到一片丛林,从一瓢一饮到人间万象,我着力于描写时代变迁中的个人感受,从个体命运中去反映地域的总体风貌和全景气象,这也是我写作的最终目标。我们都是人世间芸芸众生中的行者,而书写让行者无疆。感谢此生有文学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