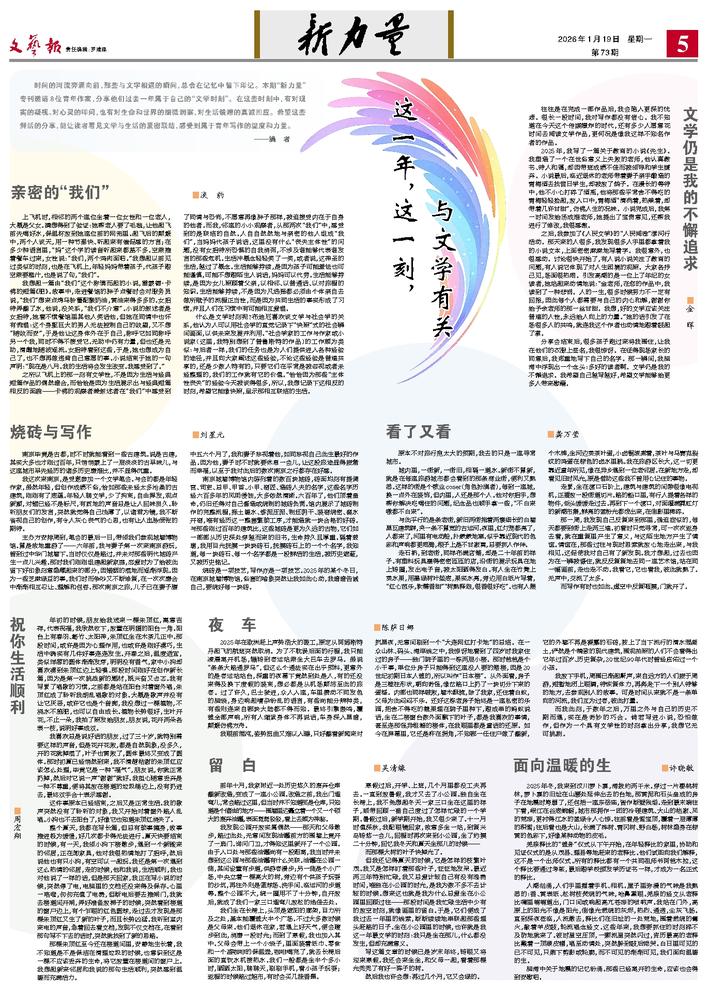上飞机时,相邻的两个座位坐着一位女性和一位老人,大概是父女。猜想得到了验证:她帮老人要了毛毯,让他起飞前先喝好水,保温杯放到她座位前的网兜里。起飞后的颠簸中,两个人谈天,用一种节奏快、听起来有催促感的方言;在多少种语言里,“妈”这个字的读音听起来都差不多。空乘推着餐车过来,女性说:“我们,两个鸡肉面吧。”我想起以前见过类似的时刻,也是在飞机上,年轻妈妈带着孩子,代孩子跟空乘要橙汁,也是说了句,“我们”。
我想起一篇由“我们”这个称谓而起的小说,雷蒙德·卡佛的短篇《肥》。故事中,走进餐馆的胖子点餐时会对服务员说,“我们”想来点烤马铃薯配酸奶油,黄油来得多多的。女招待弄翻了水,他说,没关系,“我们不介意”。小说的叙述者是女招待,她看不惯餐馆里其他人笑话他,但她在同情中也怀有惋惜:这个身躯巨大的男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又不想“随欲而安”,于是他让这身体外在于自己,称呼它如同称呼另一个我,同时不得不接受它。无助中仍有力量,但也还是无助,清醒地随波逐流。女招待看到这些,于是,她也想成为自己了,也不想再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小说结束于她的一句声明:“现在是八月。我的生活将会发生改变。我感受到了。”
之所以飞机上的那一刻有文学性,不是因为生活与经典短篇作品的偶然暗合,而恰恰是因为生活展示出与经典短篇相反的面貌——卡佛的观察者兼叙述者在“我们”中感受到了同情与恐怖,不愿意再像胖子那样,被迫接受内在于自身的他者。而我,邻座的小小观察者,从那两次“我们”中,感受到的是联结的自然。人自自然然地与亲密的他人组成“我们”,当妈妈代孩子说话,这里没有什么“丧失主体性”的问题,没有女招待所恐惧的自我消弭,不涉及谁能够代表谁发言的那些危机。生活冲概念轻轻笑了一笑,或者说,这神圣的生活,越过了概念。生活能够持续,是因为孩子可能羞怯也可能谨慎,可能不想跟陌生人说话,妈妈可以代劳。生活能够持续,是因为女儿照顾着父亲,以相邻、以普通话、以对旅程的知识。生活能够持续,不是因为凡选择都必须由个体亲自去做所赋予的流程正当性,而是因为共同生活的事实形成了习惯,并且人们在习惯中有可能相互爱惜。
什么是文学时刻呢?布迪厄喜欢谈文学与社会学的关系,他认为人可以用社会学的直觉记录下“快照”式的社会瞬间画面,以供未来发展并利用。“社会学家的工作与作家或小说家(这里,我特别想到了普鲁斯特的作品)的工作颇为类似:与后者一样,我们的任务也是为人们提供进入各种经验的途径,并且向大家阐述这些经验,不论这些经验是普遍共享的,还是少数人特有的,只要它们在平常是被忽视或者未经整理的,我们的工作就有它的价值。”恰恰因为那些“主体性丧失”的经验今天被谈得很多,所以,我想记录下这相反的时刻,希望它能像快照,呈示那相互联结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