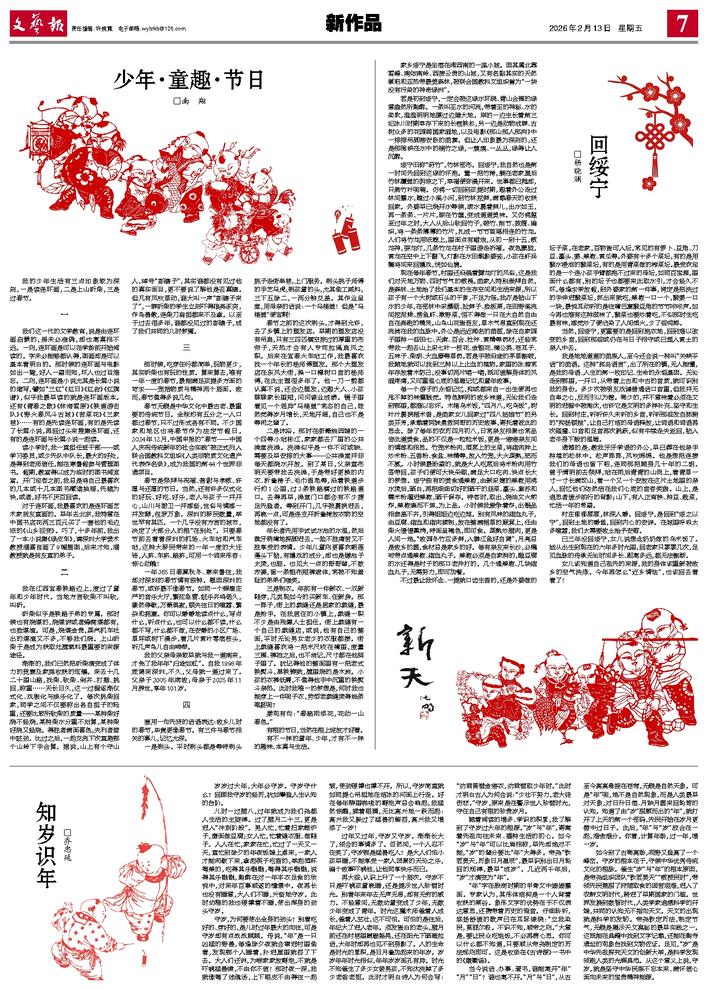家乡绥宁是坐落在湘西南的一座小城。因其属北靠雪峰、南依南岭、西接云贵的山城,又有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和亚热带最美森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一块没有污染的神奇绿洲”。
若是初到绥宁,一定会被这绿水环绕、青山合围的绿意盎然所陶醉。一条叫巫水的河流,带着巫的神秘、水的柔软,澄澄明明地漂过边陲大地。岸的一边生长着第三纪冰川时期幸存下来的长苞铁杉,另一边是动物成群、古树众多的花园阁国家湿地,以及电影《那山那人那狗》中一排排吊脚楼安卧的苗寨。但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那倒映在水中的楠竹之绿,一簇蔟、一丛丛,绿得让人沉醉。
绥宁旧称“莳竹”,竹林密布。回绥宁,我自然也是第一时间先回到这绿的怀抱。置一把竹椅,躺在老家屋后竹林覆盖的阴凉之下,幸福便弥漫开来。世事都已抛却,只剩竹叶呢喃。仿佛一切回到孩提时期,跟着外公走过林间露水,蹚过小溪小河,到竹林挖笋,满载春天的收获回家。外婆早已烧开水等候,滚水裹着笋儿,出水如玉,再一条条、一片片,晾在竹筐,变成道道美味。又仿佛越至过年之时,大人从后山砍回竹子,破竹、削节、披篾、编织,将一条条薄薄的竹片,扎成一节节首尾相连的竹龙。人们将竹龙用纸糊上,里面点有蜡烛,从初一到十五,敬龙神,耍龙灯,几条竹龙在村子里游走祈福。夜色朦胧,黄龙在空中上下翻飞,灯影在水田靓影婆娑,小孩在虾兵蟹将间来回嬉戏,恍如仙境。
现在每年春节,村里还沿袭着舞龙灯的风俗,这是我们对天地万物、四时节气的敬畏。苗家人特别崇拜自然,是森林、土地给了我们基本的生存空间和生活来源,所以孩子有一个大树或石头的干爹,不足为怪。我亦是钻山下水的少年,在密林中采蘑菇、扯笋子、捡板栗,在田野溪流间挖泥鳅、捞鱼虾、揪野菜,恨不得做一只在大自然自由自在奔跑的精灵。山鸟山花皆吾友,草木气息直到现在还流淌在我的血脉中。外公是远近闻名的苗医,除在自家园子里种一些田七、天麻、百合、杜仲、黄精等药材,还经常带我一起去山上采七叶一枝花、金银花、蒲公英、苍耳子、五味子、柴胡、大血藤等草药。若是手被沿途的茅草割破,我随地就可以找到三种以上止血的植物。家里的冰箱常年存放着木防己,没事切两片嚼一嚼,既可缓解身体的风湿疼痛,又可重温心底的温暖记忆和童年故事。
每一个游子的永恒记忆,抑或都来自一出生便再也甩不掉的味蕾触觉。特色鲜明的故乡味道,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难以忘怀。木桶乌米饭,“四月八,吃乌饭”,树叶汁裹挟稻米香,是苗家女儿回家过“四八姑娘节”的另类芬芳,承载着阿妹勇救阿哥的历史故事,寄托着彼此的思念。除了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日常亲友相聚也常品尝此道美食,品的不仅是一粒粒米饭,更是一缕缕亲友间的情感和相思。竹笼米粉肉,酒席上的主菜,将猪肉拌上炒米粉、五香粉、食盐、味精等,放入竹笼,大火蒸熟,肥而不腻。小时候最盼望的,就是大人吃席后将米粉肉用竹签带回,孩子们便可大快朵颐,满足大口吃肉、快点长大的梦想。绥宁独有的美食通辣椒,由新采摘的辣椒用沸水烫后,晒白,再把细细切好的晒干的韭菜、藠头、紫苏和糯米粉灌进辣椒,晒干保存。待客时,取出,烧油文火煎炸,辣椒燥而不焦,为上品。小时候我爱争着炸,出锅品相参差不齐,引得姐姐边吃边骂。别有风味的猪血丸子,由豆腐、猪血和猪肉揉制,放在铺满稻草的簸箕上,任由柴火慢慢熏烤,待面呈褐色,即可食。蒸熟炒腊肉,更是人间一绝。“故园冬竹应多笋,入馔江鱼好自调”,月亮总是故乡的圆,食材总是家乡的好。每有亲友来长沙,必嘱咐带点通辣椒、猪血丸子。辣椒必须是自家种的,酿豆腐的水还得是村子的那口老井打的。几个通辣椒、几块猪血丸子,无需努力,即可加餐。
不过最让我怀念、一提就口齿生香的,还是外婆做的坛子菜。在老家,百物皆可入坛,常见的有萝卜、豆角、刀豆、藠头、姜、辣椒、黄瓜等。外婆有十多个菜坛,有的是用酸水浸泡的酸菜坛,有的是用青菜做的榨菜坛。最受欢迎的是一个连小孩手臂都抱不过来的母坛,如同百宝箱,里面什么都有,别的坛子也都要来此取水引,才会经久不坏。每逢求学放假,到外婆家的第一件事,肯定是把洗过的手伸进酸菜坛,抓出来就吃,辣椒一口一个,酸姜一口一块,最悦耳动听的是往嘴巴塞酸豆角的节节咔咔声。如今再也难有这种滋味了,酸菜也要炒着吃,不似那时生吃最有味,感觉炒了便沾染了人间烟火,少了些纯粹。
当然,回绥宁,更重要的是回到胞衣地,回到难以改变的乡音,回到那些或仍在与日子相守或已埋入黄土的亲人中去。
我是地地道道的苗族人,至今还会说一种叫“关峡平话”的苗语。这种“孤岛语言”,出了所在的镇,无人能懂,是我的母语、人生的第一枚印记、生命的永恒基因。无论走到哪里,一开口,从带着上古和中古的音质,就可识别我的身份。多少次被朋友戏谑普通话口音重,但我并无自卑之心,反而引以为傲。稀少的,并不意味着必须在文明的进程中被淘汰,也许它是文明的多样补充、坚守和生长。回到村庄,听听许久未听的乡音,听听那些发自肺腑的“抑扬顿挫”,让自己打结的母语释放,让词语和词语再次碰撞、口音和足音再次跳跃,似有牛犊走失返回,钻入老牛身下般的温暖。
遗憾的是,教我牙牙学语的外公,早已葬在他亲手种植的松林中。松声阵阵,风吹绵绵。他是想把连接我们的母语也留下吧,连同那把随身几十年的二胡。曾于清明前去祭拜,站在雨后青青的山岗上,看青草一寸一寸长满坟山,看一个又一个安放在这片土地里的亲人,回忆他们依然活在我们心底的音容笑貌。山上,是追思者缓步前行的背影;山下,有人正育秧、种豆、栽菜,忙活一年的希望。
村庄郁郁葱葱,林深人静。回绥宁,是回到“绥之以宁”,回到土地的静谧,回到内心的安详。在城里呼吸太多喧嚣,我们太需要故土给予安慰。
已三年没回绥宁,女儿说想念奶奶做的乌米饭了。她从出生到现在的六年多时光里,回老家只寥寥几次,足见血脉的传承无论时间多长、距离多远,都无法割断。
女儿该知道自己祖先的来源,我的身体该重新被故乡的空气洗涤。今年再怎么“近乡情怯”,也该回去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