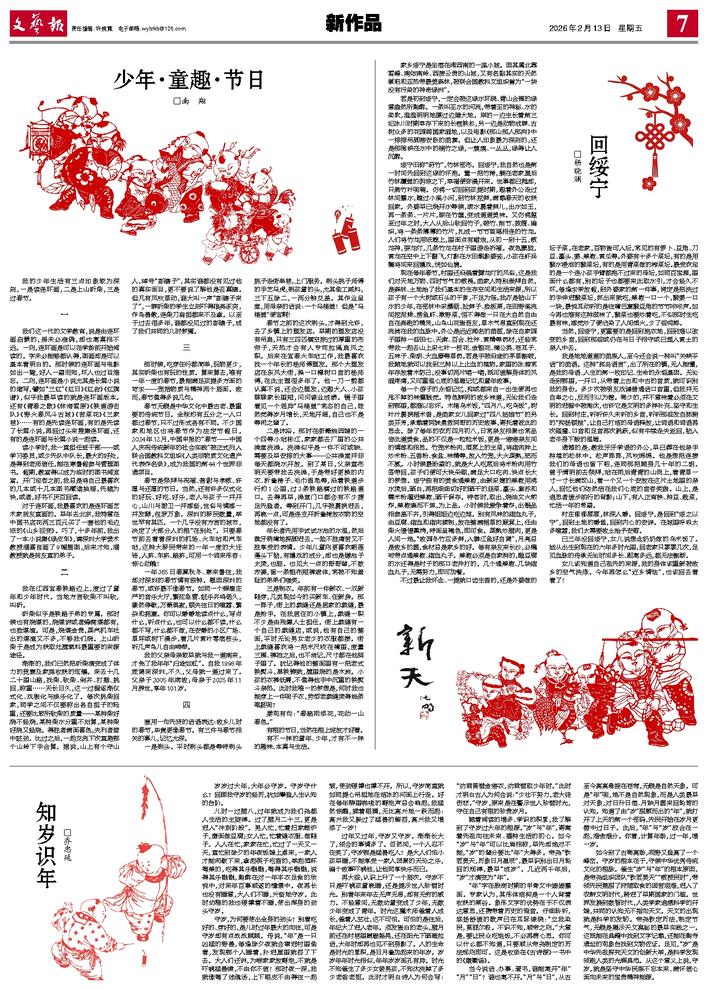我的少年生活有三点印象较为深刻,一是读连环画,二是上山斫柴,三是过春节。
一
我们这一代的文学教育,说是由连环画启蒙的,虽未必准确,却也离真相不远。一则,连环画是可以在学龄前开始阅读的。字未必能够都认得,图画却是可以基本看明白的。那时候的连环画与电影如出一辙,好人一望而知,坏人也过目难忘。二则,连环画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缩写,譬如“三红”《红日》《红岩》《红旗谱》,似乎我最早读的就是连环画版本。还有《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三家巷》……有的是先读连环画,有的是先读了长篇小说,再回过头来搜集连环画,还有的是连环画与长篇小说一起读。
读小学时,我一直担任班干部——或学习委员,或少先队中队长,最大的好处,是得到老师信任,能在寒暑假参与管理图书。假期,教室得以成为临时的图书阅览室。开门迎客之前,我总是将自己最喜欢的几本或十几本图书藏诸抽屉,先睹为快,或者,好书不厌百回读。
对于连环画,我最喜欢的是连环画艺术家贺友直画的。早年去北京,我特意在中国书店花两三百元买了一套他的毛边纸的《山乡巨变》。巧了,十多年前,我出了一本小说集《绿皮车》,请深圳大学美术教授潘喜良画了9幅插图,后来才知,潘教授就是贺友直的弟子。
二
我在江西宜春铁路边上,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当地方言砍柴不叫砍,叫斫。
斫柴似乎是铁路子弟的专属。那时候也有烧煤的,烧煤饼或者蜂窝煤都有,也捡煤渣。可是,烧煤金贵,蒸汽机车吐出的煤渣又不多,不够我们烧。上山斫柴于是成为获取灶膛燃料最重要的来源途径。
渐渐的,我们已然把斫柴演变成了体力的竞赛及家庭收获的炫耀。来去十几二十里山路,找柴、砍柴、剁齐、打捆、挑回、称重……天长日久,这一过程逐渐仪式化、戏剧化与娱乐化了。每次挑柴回家,同学之间不仅要称出各自担子的轻重,还要比较所砍柴的质量——某种柴好烧不经烧,某种柴水分重不划算,某种柴好烧又经烧。得胜者满面喜色,失利者暗中鼓劲。比过之后,一起交流下次直趋哪个山岭下手合算。据说,山上有个守山人,绰号“彭瞎子”,其实谁都没有见过他的真实面目,更不要说了解他是否真瞎。但凡有风吹草动,谁大叫一声“彭瞎子来了”,一群斫柴的学生立刻吓得狼奔豕突,作鸟兽散,连柴刀扁担都来不及拿。以至于过去很多年,谁都没见过的彭瞎子,成了我们共同的儿时梦魇。
三
那时候,吃穿住行都简单,玩物更少,其实斫柴也有玩的性质。算来算去,唯有一年一度的春节,最能满足孩提多方面的苛求——笼括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故而,春节值得多说几句。
春节无疑是中华文化中最古老、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全球约有五分之一人口都过春节,只不过形式各有不同。不少国家和地区也将春节作为法定节假日。2024年12月,中国申报的“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我国的第44个世界非遗项目。
春节是祭拜与祝福、答谢与孝敬、许愿与还愿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仪式化的好玩、好吃、好乐,老人与孩子一并开心,山川与厨卫一并感奋,世俗与情感一并发酵,包罗万象。深圳的移民数量,举世罕有其匹。一个几乎没有方言的城市,决定了大部分人的根“在别处”。只要春节前去看看深圳的机场、火车站和汽车站,这种大移民带来的一年一度的大迁徙,人挤、车挤、路挤,可用一个词来形容:惊心动魄!
一年365日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我却对深圳的春节情有独钟。概因深圳的春节,或许最不像春节。如同一个辉煌庄严的音乐大厅,繁弦急管、鼓乐齐鸣偌久,骤然停歇,万籁俱寂,顿失往日的喧嚣、繁杂和拥塞。你可以静静地读点什么,写点什么,听点什么,也可以什么都不读,什么都不写,什么都不做,在安静的小区广场、草坪或树下漫步,看几片黄叶零落枝头,听几声鸟儿自由啼啭。
我的父亲母亲较早就与我一道南来,才免了我年年“归途如虹”。自我1998年底调来深圳,不久,父母就一道过来了。父亲于2005年病故;母亲于2025年11月辞世,享年101岁。
四
套用一句先贤的话语表达:故乡儿时的春节,毕竟更像春节。有三件与春节相关的事儿,记忆尤深。
一是剃头。平时剃头都是等待剃头挑子走街串巷,上门服务。剃头挑子师傅的手艺马虎,剃孩童的头,尤其偷工减料,三下五除二,一两分钟交差。其作业呈堂,用母亲的话说:一个马桶盖!但是“马桶盖”便宜啊!
春节之前的这次剃头,才得到允许,去了乡镇上的理发店。早期的理发店没有吊扇,只有三四匹横空掠过的厚重的布帘子,天热才会有人专司拉绳扇风之职。后来在宜春火车站工作,我最喜欢找一个年长的杨师傅理发。那个大理发店在东风大街,操一口樟树口音的杨师傅,在此主理很多年了。他一刀一剪都认真不说,还会边理发,边跟大人、小孩聊聊家长里短,问问课业成绩。镜子里看见一个迥异“马桶盖”常态的自己,陡然觉得岁月增长,天地开阔,自己也不是等闲之辈了。
二是沐浴。那时在浙赣线西端的一个四等小站彬江,家家都去厂里的公共澡堂洗澡。洗澡似乎是一件不可或缺、需要及早安排的大事——公共澡堂并非每天都烧水开放。到了某日,父亲宣布明天要带我去洗澡,于是带好更换的内衣、折叠椅子、毛巾香皂等,沿着铁道步行约1公里,过3条铁路横过的铁路道口。去得再早,澡堂门口都会有不少捷足先登者。等到开门,几乎被裹挟进去,再晚一点,可是连支开折叠椅放衣物的空地都没有了。
年长者先用手试试水池的水温,然后龇牙咧嘴地探脚进去,一脸不胜痛苦又不胜享受的表情。少年儿童则更喜欢朝莲蓬头下钻,有嬉戏的成分,却也是嫌池子太烫,也脏。也见大一点的哥哥辈,不敢赤裸,留一条粗布短裤遮体,常被不知羞耻的弟弟们嗤笑。
三是制衣。年前有一件新衣、一双新鞋穿,几类现如今的买新车、住新房。那一阵子,街上的裁缝还是居家的裁缝,最是抢手。在我居住的小镇上,裁缝一职不少是由残障人士担任。街上裁缝有一个自己的裁缝店,或说,他有自己的铺面,平时无论男女老少的衣服都接。街上裁缝喜欢将一把米尺咬在嘴里,度量三围、裤裆之后,也不消记,尺寸都在他脑子里了。犹记得他的铺面里有一把老式铁熨斗,黑铁铸就,膛里烧的是木炭。小孩的衣裤低廉,不值得他手中沉重的铁熨斗亲热。此时我唯一的梦想是,何时我也能穿上一件呢子衣,劳烦老裁缝烫得线条笔挺呢?
秦观有句:“春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
有根的节日,当然在根上绽放才好看。
有不一样的童年、少年,才有不一样的趣味、本真与生活。